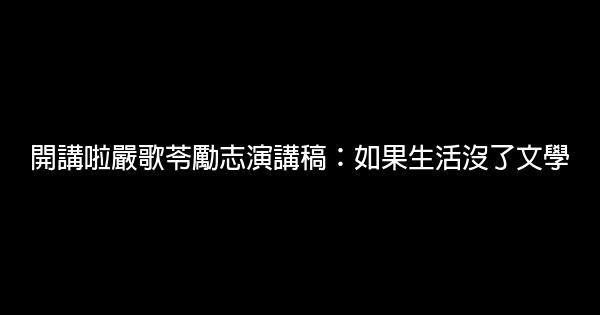想到一个在美国的一个朋友的儿子学中文,说“陆陆续续”是什么意思,“陆陆续续”意思是“慢慢的,慢慢的”。后来那孩子就造一个句子,“天快黑了,爸爸陆陆续续地回来了”。
我总说,中国在二十多年前,是非常贫穷的,是世界上有名的贫穷的国家,但这么贫穷的生活,给了我们这代人的是非常非常多的,富有的故事。我们每个人都是一座故事的富矿,能够开采出很多故事来。我觉得出生在我这样一个家庭里,我的父亲是一个作家,我的爷爷曾经是个作家,所以如果不做作家,倒是也奇怪了。我的父亲跟我说,你是为文学生的。人家问他,你这辈子最好的作品是什么,他就回答了一句,“我的一生最好的作品是我女儿”。他就是《铁梨花》的原作者,他叫肖马,后来他说“我最近改名字了,改成肖也是”,人家说“你为什么改成肖也是呢”,他说,人家介绍我都说了,“这是严歌苓,这是肖马先生,也是作家”,他说“我就是肖也是”。就是这么个老爷子,特别好玩。他去年去世了,所以我今天的讲话,也是为了纪念他。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爸爸是拉小提琴拉得挺好的,然后画画,画油画也画得很好,他的写作也写得很好,所以他是非常多才多艺的。每次从外面回来到家里,第一个曲子就是……就是这么一个梦幻曲,所以我爸爸这一辈子就是活在梦幻曲当中的这么一个人。我爸爸的图书室呢,全世界的经典都有。我爸爸对我态度就是你爱看什么看什么,那我妈妈就说,你要看看女儿在干些什么,整天都在看些什么东西,乱七八糟的。我爸爸就说,孩子要看什么就看什么。我最爱看的是《唐璜》、《战争与和平》,当然《战争与和平》这样的小说我只看和平不看战争,就是看他们谈恋爱的这些地方。《唐璜》是非常好看,又有历险,又有爱情。后来我就跟小朋友们讲故事的时候,我连没看的地方,我都把它都给加上了,让那故事连起来,所以那时候我最开始创作的最初期。我妈妈是个话剧演员,我就记得小时候,她就给我背莎士比亚,罗密欧,罗密欧,什么什么的,哄我睡觉的时候。实际上他们没有打算让我做作家,或者干嘛的。
小的时候大家都说,你的条件很好,你可以去唱歌,你可以去跳舞,我就一直以为是一个应该在舞台上过完一生的人。后来发现跳舞也不行,唱歌也不灵,突然有一天就发现我可以写作,就是在中越自卫反击战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不到二十岁吧。然后我就说我要到前线去,当然那时候女兵不能到前线,那你就到前线的包扎所吧。然后我就去了以后,看了一千多个伤兵,一天晚上抬下来,所以这种时候对我催化的那种成熟一下子就发生了。战争胜利了以后,我就觉得跳舞这种东西已经不足以表达我自己,我一定要用其他的方式来表达,那么什么样的方式呢?那就是写作。当时这种特派记者到前线去,要写一些小报导,因为当时没有那么多记者,就那么一个突然的转折,使我成了一个部队的创作员。
后来我到了1989年的时候,我就觉得应该有另外一个地平线,来开始作为作家的新的一个起跑点。当时我要考托福,要知道当时我的英文只会abc,根本就不能够达到要求,出国就是不可能的事。那我怎么办呢,我就拿了三本《新概念英语》,我每一本都背下来了,然后胳膊上都写满了单词,然后整天就在餐馆里打工的时候看一眼,看一眼这,看一眼那,然后就把单词也这么背下来。到了美国我第一次考试,我就记得,人家说你能考过500分就不错了,就你这样学英文。后来,我第一次考了540分,当时的研究生要550分最底线。后来我就上了个强化班,看看能不能弄到600分,因为如果我今年考不上奖学金,那就意味着这一年我还得学英文。托福在同一个时期,每个城市都有考场,我在buffalo考完一场以后,我又飞到纽约考一场,然后再飞到芝加哥考一场,这样的话,我可以拿到一个最高的,这三个考场里,拿到一个最高的分数。这样的话,我就考了一个577分,我就拿到了全奖学金,真是没白吃苦。
那个时候,我特别逗的是我要给人家当佣人,就因为学校的这个奖学金只包括学校的用费,学费什么的。我没有钱生活,要吃要住,我就给人家当保姆。记得是台湾一个挺有钱的人家,他们家有个小男孩才2岁,那小孩很皮。我第一天去就给他拖地板,一拖,那小男孩把刚给他换的白袜子,“砰”就跳上来了,然后一看那白袜子全是水,然后再给他换下来,然后又给他拖地板,一动他就跳,然后那袜子又湿了。有一次他一跳,我赶快一抽,就听见“砰”的一声,一看坏了,整个天花板裂了。我一想,完了,我说我这挣一个月的钱,肯定不够赔天花板的,对吧。怎么办呢,等女主人、男主人从外面回来,我想说天花板被我弄碎了,对不起,但每天都是不敢说。但是发现,他们为什么也不找我说这事。我就一天天开始想往下混,有一天他说我们家要来客人了,你要给我们做一条松鼠桂鱼。我说好吧,我凑合看看怎么做的。那鱼一放进去就沾底了,怎么办,我“哗哗”一晃那个锅,“哗”那油就全溅起来。我满脸都是油,就全部烫伤了。然后那女主人就赶快拿出冰,就放在我的脸上、脖子。脸上都烫了很多,烫伤。后来我心想,我说我可以走了。但是我告诉你,你也别给我钱了,我说这个天花板被我弄坏了。后来那个女主人说,我们刚搬进来,天花板就破了,我们就一直想修,但一直没修。哎哟,我才知道,这天花板不是我弄破的,人家搬进来就是一个破的。后来我想,我辛辛苦苦,天天给你们做啊,做啊,然后就是希望到我走的时候,你们不要跟我说这天花板,别骂我就行了。所以那个时候我从一个中国作家协会的会员和两本小说都得了奖的一个年轻女作家到国外,就能够有这么大的落差,就是为了一个挣钱,能够养活自己,做一个独立的学生,然后把功课学好。就那个阶段在美国,我觉得每天就像竹子一样,拔节,很快!等我拿到了mfa的时候,我就觉得最痛苦的,最最难熬的日子结束了。
还忘了告诉你们一件事,我一个幼稚园的好朋友,介绍了我一位男朋友,他是美国的一个外交官。到了年底,这个美国外交官要汇报他结交的人,然后他就写到,填了一个“认识一个中国女孩”,这个性质是什么,也有个abc的选择,然后就勾了一个“结婚对象”,要跟我结婚的。填了这个表一递上去,好了,美国的fbi,我功课那么忙,每个星期都要跟他们谈话。你小时候干嘛的,你爸妈干嘛的,谁给你介绍这个人的……然后这个都弄完了,可是他们还是对我耿耿于怀,不知道为什么。最后就跟我说,我们决定要对你进行一个测谎试验,我老公一听就炸了,他说这绝对是一个侮辱,他就不做了。把这个外交官的牌子,进国务院大门的那个,剪成四半,放在一个信封里,放桌子上走了。我说,哎哟,你怎么让我失去一个这么好的体验机会,我特想知道他到底测不测出来谎啊,我说这是一个多么有意思的经验。我老公说,你的生活还不够有意思的?这就是我在美国的第二个特别有趣的阶段。
1992年忽然接到一个电话,他说我是导演《喜宴》的李安,他说我想跟你买一部小说的著作权,《少女小渔》。当时我就,当时那一笔钱,我觉得好大的数目,可以让我挺无聊的写好长时间的小说,是吧。同一年就有三个人来买我的著作权,一个叫李翰祥,香港的。然后接下来就是朱延平,是一个台湾导演。所以在同一年,我有三个剧本著作权卖出去了。这样子的话,我在海外就变成了一个应该讲就是专业的作家吧。
而每到一个地方,每一种文化,每一种语言,使你不断地来感受中国语言,就觉得这个华语,确实是人类最美丽的一种语言。所有语言都是听的,只有华语是图像的,它从最开始的象形发展出来,所以我们的语言是看的,所有这个我觉得非常了不起。我们学校教俄国文学经典的一个俄国老师说,世界上有三本小说一定要读,当中第一本他提到就是《红楼梦》,第二本就是列夫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然后第三本就是雨果的《悲惨世界》。可是我就觉得,看完了《红楼梦》的翻译以后,我就觉得那人家怎么能够把曹雪芹的那种禅机,他那种禅意,再加上他吃喝玩乐的描述,中国文学里的思想,怎么能够去让西方人来欣赏,我就觉得这真实太难了。
我自己用英文写小说,也把自己的小说翻译成英文,在翻译过程中,它必定要失去那么多,所以我就觉得,我还有余生,可以希望能够做一个哪怕是一个独木桥,在这两种文化之间,能够起那么一点点作用。当然我知道真的是太难了,中国语言确实是太棒了!因为我觉得我的生命就需要一种浓烈度,只有写作能够给我,就是你不求后果,你不求一种利益,不会使你烦恼,所以写作是给你这样一个世界。你可以让你的人物来宣泄的,其实你最秘密的情感。当然最最根本的一点是,我想把中文写成一个,就是能够通过我的手来创造,很有严歌苓风格的中文。
今天要讲的还很多,但是时间有限制,今天我的演讲就到这,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