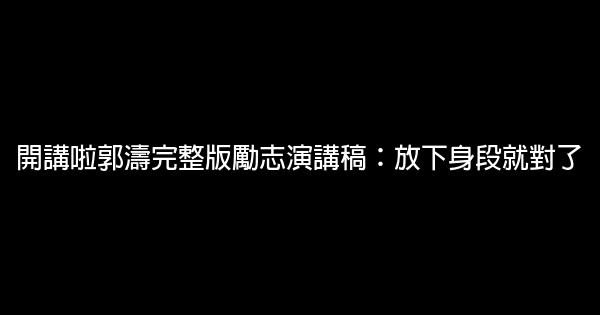来这儿之前有点紧张,我在二十多岁的时候认为我自己是一个叛逆者,一个愤怒青年,对很多东西都看不惯,有自己的想法。我记得当时上大学的时候,最爱好的几件事情。第一:我喜欢摇滚乐,因为那个时期,中国的摇滚乐风起云涌,我们会感觉到非常地刺激和亢奋,我听到那些音乐后就会很躁动。我记得听平克·弗洛伊德《迷墙》的时候,我整晚整晚地睡不着觉。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那么骚动,我为什么要那么愤世嫉俗,那么生气?还有就是喜欢跟我的一些哥们儿、好朋友们一起排演实验戏剧,我们认为实验戏剧就是反叛,就是把传统的戏剧反过来,用这种方式来表达自己作为一个年轻人的一种想法,一种爆发。
我记得当时排演一个校园戏剧,也叫实验戏剧,叫《等待戈多》。那个时候,非常地穷,真的穷得可以说叮当乱响。一千块钱演出一个话剧,你们相信吗?我们这些哥们儿,晚上饿得实在不行了,大家就用一个大锅来煮速食面吃。可能石头喜欢速食面,就是因为遗传我这一部分吧。速食面也没有什么营养,然后在里头随便打几个鸡蛋,没有菜,我们就翻墙出去偷菜,偷完菜回来以后,把外头的白菜帮子全撕掉,把里头的菜心拿手一抓,就放锅里煮,感觉非常地香,非常地好吃,那是我吃到最好吃最好吃的面条。
那种经历虽然很辛苦,但是大家确实是在一种很亢奋的创作状态里去做事的,当然的确受到了很多人的关注,尤其是很多的女孩子。就觉得你们这些人太厉害了,居然不吃饭还能够天天排演出这么好的戏,自己感觉到很荣耀,还有很多的满足感。
大学毕业以后,我又非常顺利地跟张艺谋导演、冯小刚导演合作了几部电影。我的起点很高,所有人都对我敬而仰之,把我当成戏剧学院的一个奇才,我的老师们都说,下面的同学你们看一看,这就是我教出来的学生,他现在怎么怎么样。那时候我感觉自己在一种不可思议的、莫名其妙的荣耀和自尊心的满足里生活。
记得当时我住在一个非常小的平房里,那是我们单位分的宿舍。排队的那些采访记者,大概(多到)拐出胡同来,那个时候自己真的有一种很骄傲的感觉,觉得我终于出名了,我终于长大成人、证明自己了。但是到了大概不到三十岁的时候,那个时候的中国电影也是进入到了一个低谷,很多的片子来找我,是我不太满意的,也是不想接的。
我记得有一次是一九九几年的时候,我在上海。有一个戏我是(同时)演了一个哥哥和弟弟,是双胞胎,非常有意思的哥哥在上海滩是白道,弟弟是黑道。两个人在互相地打,那我白天拍哥哥,晚上拍弟弟,这样没完没了地一直在拍,结果拍到后来,我说,不行导演,我坚持不住了,你让我休息一下好不好?好吧,晚上回去睡不着觉,自己一个人走在上海的小街道上,没有任何人,买了一点啤酒,一边走一边自己在想,我白天演哥哥,晚上演弟弟,我是谁?那时我真不知道我是谁,我郭涛到哪里去了,所以当时我的精神状态,大概就是这样的,有点找不着自己,有种迷茫的感觉。
可能在座的朋友都不知道我是一个离异家庭的孩子。我记得在我小的时候,(家里)更多的是争吵打闹,我不知道一个正常的家庭生活是什么样的,我未来的情感是什么样子,非常迷茫,有的时候也很痛苦。我想可能这种迷茫一直延续到我大概二三十岁的时候,我不知道自己的未来,自己的另外一半,自己的很多很多的想法是怎么样的。可能是因为前面的工作给我带来的那种荣誉或者是收获,太迅速,太快了。我在这种迷茫的过程中,好像真的找不到一个途径,总感觉自己前面是黑黑的一条道,始终往前走,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是自己不停地一直要努力地往前走。
我记得有一次孟京辉来找我,他想排一个话剧,在1999年的时候,话剧的名字叫《恋爱的犀牛》。我那个时候在开一个酒吧,因为我喜欢喝酒,总是想在那种比较迷茫的时候,用酒精的方式来刺激自己,让自己睡着,让自己麻木一点。每天把自己喝得烂醉,晕乎乎地回家,好去忘掉自己在当时的烦恼。我看到孟京辉的时候,我一个人在酒吧的舞台上跳舞,一边喝着酒,一边在跳,一个人跳了一个多小时。跳完以后,我满身是汗,其实更多的是泪水,那个时候孟京辉拍着我的肩膀,他说,XX年新的世纪,马上就要到来,我们难道不做点什么吗?你就想天天这样去喝酒,天天在这样一个灯红酒绿的环境下宣泄自己吗?你原来对於戏剧、对艺术的追求,到哪里去了?说得我好像感觉有点毛骨悚然,因为确实我当时的精神状态和生活状态都不是太好。我就在想,那么我们排演一个话剧吧。这个话剧我不是为你,也不是为我。也许是在为我的心中的那个人,去较劲,去做一件事情,来证明自己吧。
那个戏,到现在为止对于我来说,其实更多的是一种愤怒,一种宣泄。就像在剧中的马路,这个人物一样,女孩子不爱你,你为什么还要没完没了地去追求她,其实就是好像自己跟自己在较劲。新世纪来临了,一切没有改变,过去是什么样子还是什么样子。我说我该怎么办,下面,还要去再排演一些你自己认为好的东西吗,还是随波逐流就这样走下去?
XX年初的时候,又遇见了我人生当中,非常好的一个哥们儿,那就是宁浩导演,于是乎就出现了《疯狂的石头》这部作品。我记得非常清楚,第一次见面交流的时候,他在不断地跟我讲戏,他说哥们儿,你来演这个戏吧,你是我见过最牛的演员,我是看着你戏长大的。说了一个多小时以后,我脑子飞了,我就在想,他跟我说的这个戏,我怎么好像似曾相识啊,这个角色,好像就是为我写的似的。这对我来说是个机会,你不是就是想要做这样的戏吗?你不是就想干这样的事情吗?有这样一批好哥们儿,大家一块儿去努力做嘛,自己想飞了,想开了。后来脑子回过神来的时候,导演说大哥,你觉得这戏怎么样,我说好,但是我没听懂,我说不过没关系,我很喜欢这个戏,我们来一块儿玩吧,他说好吧,那就一块儿玩吧。
于是乎我们就开始干了,那个戏只有三百万,所有的人不计片酬,每天都在一种非常开心快乐的,非常放得下、放得开的情绪里去创作,跟黄渤、桦哥,我们一起吃火锅,然后出去蹦迪,喝酒。后半夜说拍你的戏了,直接杀过去拍戏,所有的东西都那么的放松、自然、开心,没有想过任何的外在东西,说我要在这个戏里,多么的出名,将来我在颁奖礼上要说感谢谁谁谁,从来没有想过那样的话,从来没有想过。
我们自己掏钱租了一个酒吧,动员所有身边的业内人士说来看这个戏,给我们做做宣传。那时候感觉,就像是我重新开始起步,从我第一部戏那样的一个起点开始做起,一点一点地把《疯狂的石头》展现给了大家。但是在那个过程当中,我跟我的这帮哥们儿,结下了一生的友情,可以说我现在跟黄渤、跟宁浩我们可以不再见面,我们平时也不打一个电话,但是只要宁浩一个电话,你让我演一个死尸我都愿意,真的。我就是这样一个人。
关于我情感的归属,我一直非常地纠结,也非常地拧巴。直到有一天,我见到了我现在的爱人,她是一个学理工的。这在我过去是绝对不能够接受的一种人群,因为我是搞艺术的嘛,搞艺术的人一定是(生活)在一种鲜花,浪漫,音乐,掌声里。而她呢,往往我跟她讲,哇怎么怎么怎么样的时候,我说你能明白吗,她说你喜欢就好。最有意思的一次经历就是,我跟我母亲的关系虽然很好,但是难免会母子之间会有一些矛盾。有一次我在开车出去的时候呢,我的女朋友在后面,我母亲在我的旁边,我开着车,因为很小的一件事情争吵起来了。可能因为我们都是搞话剧的,声音比较响亮,然后跟她越说越激动,而且有点危险,在三环路上。这时候我通过反光镜,看了一下我老婆,我后来的老婆,她(居然)睡着了。我不知道是怎么样一个(女孩),好像、也许是老天爷,给予我们的安排,碰到了她这样一个非常温柔、体贴的,能够懂你的心的,而且能够融化你的这样一个女孩子,我感到我很幸运,真的。
一个男人的成长有的时候是需要一种精神来寄托的。比方说,你有特别拧巴的时候或者是特别有奋进、有想法的时候,一定要放下架子,放下包袱,努力往前走。但是我不希望大家去较劲,因为我就是一个较劲的人,我用十年给我换来的经验,在这里,也许可能对某些跟我同样经历的朋友们会有所启迪,有所帮助。生活不能够较劲,放下来才能够走得更长远,平实的生活才能让你感受到真实的情感;爱人不一定是非要轰轰烈烈,山盟海誓的,适合你的就好,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