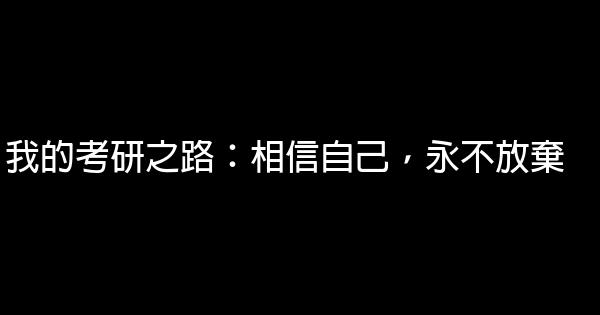文/王江涛
1996年,我在一家政府机关工作,待遇不错,可以分房,但无法适应机关生活,决意考研。当时仔细考虑自己的实际情况,生性自由散漫,也不适合公司工作,最喜欢做一名大学教师。由于从小倾慕北大,自幼喜爱古典文学,决定报考北大中文系古典文学专业,专攻魏晋隋唐文学方向,以后争取留校任教。当时并没在意,自己是跨城市、跨校、跨专业考研,难度极大。
1996年9月,专程前往北大,咨询考研信息。中文系只提供专业课参考书,没有历年试卷,不提供导师联系方式,很是郁闷。目睹全国各地的莘莘学子前往中文系,立志考研,压力不小,毕竟只是个人兴趣,从未专业学过。好在有位高中同学毕业于北大中文系,所以冒然找到中文系研究生宿舍楼,寻找熟人。碰巧同学的朋友正在中文系读研,了解了很多情况,准备报考钱志熙先生的硕士。钱先生是葛晓音教授的弟子,袁行霈教授的再传弟子,仰慕已久。晚上借宿于朋友的宿舍。
第二天上午,在朋友的宿舍中偶然看到一份北大校报,上面有一则讯息,引起我的极大兴趣:1996年9月,国内第一个宗教学系——北大宗教学系成立了!精神为之一振。当时对于宗教的兴趣已经大于文学,感觉冥冥之中,命运在召唤我。经过深思熟虑,决意转考北大宗教学系。好在从小对于升官发财没有什么兴趣,计画硕士毕业后赴美读博,然后争取回北大任教。
当即前往宗教学系了解相关情况,当时要考五门:英语、政治、马克思主义哲学、中西哲学史和宗教学原理。由于本科学习英语,所以英语不用复习,难就难在专业课,从未接触过。北大宗教学系本是哲学系的一个专业,1996年独立成系,事实上还属於哲学系。国内传统上把宗教学作为哲学的一个分支来研究,而在国外,宗教学和哲学分庭抗礼。我一直认为,宗教类似于文学艺术,讲究感性和直觉;而哲学类似于理科,讲究理性和逻辑,两者大相迳庭。宗教学的专业课以哲学为主,不是我的长项,又是一大难关。
根据系里公布的参考书目,跑遍了北京各大书店,终于买全了所需书籍,包括赵光武先生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北大中哲教研室《中国哲学史》、南开大学《西方哲学通史》、吕大吉先生的《宗教学通论》等十多本书。
由于在职考研,工作很忙,只能利用业余时间复习。直到1996年12月,才真正开始全面复习,每天晚上回到宿舍,挑灯夜战,很是辛苦,觉得这帮哲学家真是有病,恨不得一刀捅死算了。由于智商较低,迄今仍然不知所以。考试时,专业课参考书看了一半都不到,满分500分,我取得了254分的好成绩。只有英语过了,其他四门全部挂掉,专业课平均三四十分,很是悲惨,第一年考研以大败告终。
考研失败了,单位也知道了。当时各地正在精简机构,由于我在那个单位学历最高,专业最对口,我想肯定不会是我。单位中有很多老同志,眼看就要退休了,我以为会有人提前退休。一天,领导找我谈话,问我是否知道要精简机构,我自然知道。领导告诉我,我们单位只有一个指标。我好奇地问是谁,领导严肃的说:“就是你。”当时感觉犹如五雷轰顶。我质问领导为何是我?领导说:“因为你工作态度不端正,又要考研。”我便无话可说,由于不喜欢机关工作,我在班上经常看一些《太平广记》之类的闲书,还把英国作家劳伦斯的禁书《查泰来夫人的情人》翻译了三分之一,后来觉得出版可能性不大,全部销毁。
当时决意考研,不想在机关混一辈子,便向单位请了半年假,回家复习。单位允许我带薪复习,但告诉我如果明年再考不上,工作也就没有了。我和父母压力都很大,好不容易大学毕业,找了一个还凑活的工作,眼看就要没了,考研并没有很大的把握。好在父母非常开明,并未表现出来。
1997年7月,再次回到父母身边,面临第二次“高考”。7月至9月复习得还可以,不幸的是,九月份问题出现了。由于父母觉得我很艰苦,每天给我订了牛奶补充营养。从小家中清苦,没有喝过牛奶。每天早上起床,我一般不吃早饭,先空腹喝下一斤牛奶,偶尔吃个鸡蛋。喝到9月,胃开始出毛病了,每天腹涨,吃的东西完全无法消化,每天基本无法进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