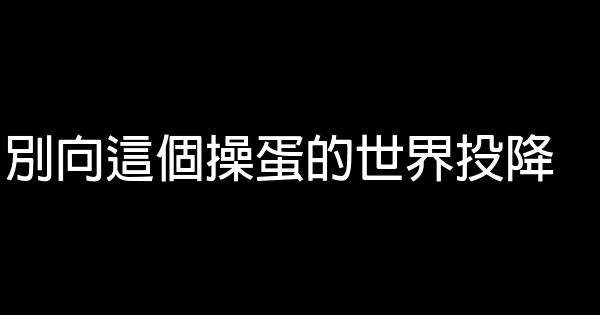文/唐山
想来毕业已三月有余,同学大都结伴而南飞,唯我一人孤雁北征,这最初的三个月,无论苦乐悲喜都挨了过来。可是在这真正回家的时刻我顿时悲从中来,千言万语吐不尽其中的苦涩。
不敢说自己是大学毕业,因为大学生都被某些人整得名不符实,却也不敢妄自菲薄,毕竟相较来说,自己却也是正经的大学毕业,不是专科生充大学生,不是二流学校的学生充大学生,也不是那些本就上不了大学却上了大学的人以次充好。
十一长假,空闲于家,村子小,事情很快便能传遍整条街。我打算回家的讯息也很快如是。我家分东西两院,来回之间穿过近乎整条街,途中难免遇上个人,便是一通打听。虽知不是恶意,却也令我生畏。
“放假了?”
“咋回家了?在外头不行啊?”
“家里多不好啊!在外头哪里不比家里强?你看那个谁……1万多块,……”
“开多少钱啊?……才这么点儿啊,唉!……”
他悻悻的离开,我也是,我不是!我要背着这样的一筐话回家,吃饭,看电视,睡觉,睡不着,上火,犹豫,怀疑,考量,浅睡,然后开始另一天。
秋天的清早,给人十分的爽意。每每我都打开窗户——呼吸,大口大口的吞,也许像极了喘。当时的心情特别的好,不想任何,我就是我,秋天就是秋天。
家里的人都不给我的决定任何的态度,我早已习惯了,他们相信我,可我不是那样的相信自己和他们;我希望父母是真的高兴我回家的决定;我希望哥哥不再为我的前途担忧;我希望自己能顶得住来自任何方向的压力。可是每个堤岸都不是坚不可摧的。
我在六号的时候被安排进驻工地,甲方监理。仔细想来,一个闲缺,一个锁链。经过安排我负责102号建筑,是宿舍楼,正在浇筑框架。工地上像我这样的闲人不多,而且又是新来。往哪里一走都会有人盘问几句,知是同县的人,便多说了很多话,我知道他们也没什么恶意。
“你这大学生,咋回家了?”
我深知这句话的嘲讽意味,他怀疑我的大学文凭,他怀疑我去的是一个那些不入流的学校,他认为我是在外不能找到工作才来了这里,他认为我是个不合格的毕业生。
“才这么点儿,我那个表兄的儿子在云南,……1,2万啊……”
……
我不好打断这样的话,唯有诺诺而笑。
“这穷县没啥前途,当初这个老板弄那个厂子,到现在不也就那个样么,一年赔个几十万,当初也吹的楞着呢!跟哈工大合作,……教授好像都是假的,哈哈……这个呀!……”
“有能耐的人谁在这破地方儿……!”
我不置可否,木木的呆了一整天,然后吃饭回宿舍,很早就睡了,很早就醒。疼?不是,真的不是,而是恐惧,怕自己真的就死了,死的不明不白。
我真羡慕那些没心没肺的人,他知道工作,知道给工资,就万事大吉了。我却在有工资的时候考虑没工资的情况,杞人忧天。可是现实就是天已经塌了。
每天去工地对我都是一个考验,要面对各种的闲言碎语。我诚知那些都是假的,可是当假话被身边的每个人都说上一遍,你也就信了。当初我已然料想自己会被各种的言论击中,可是它们来的比想像的苦难更加突然,更加强大。
那天浇筑一根承重的柱子。水泥砂石料放入,经振动棒的振动,原本结实的的盒子版突然就裂开了一道缝,混凝土瞬间流了出来,汩汩不断。我看着那道口子,像极了自己,压力超过了预期。原本安定的一切都流了出来,有泰山崩于前的轰然,仿佛支持一个橡皮人的脊柱突然被抽走,整个人就软塌下来,泥一样摊成一片。想自己的哪处也开了这样一条口子,支起梦想的柱子好像也在汩汩的塌下去。泪水在眼眶里乱晃,因为塔吊有了虚影,而且还在抖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