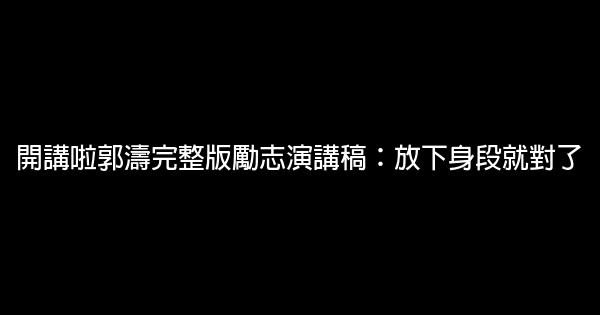來這兒之前有點緊張,我在二十多歲的時候認為我自己是一個叛逆者,一個憤怒青年,對很多東西都看不慣,有自己的想法。我記得當時上大學的時候,最愛好的幾件事情。第一:我喜歡搖滾樂,因為那個時期,中國的搖滾樂風起雲湧,我們會感覺到非常地刺激和亢奮,我聽到那些音樂後就會很躁動。我記得聽平克·弗洛伊德《迷牆》的時候,我整晚整晚地睡不著覺。我不知道自己為什麼那么騷動,我為什麼要那么憤世嫉俗,那么生氣?還有就是喜歡跟我的一些哥們兒、好朋友們一起排演實驗戲劇,我們認為實驗戲劇就是反叛,就是把傳統的戲劇反過來,用這種方式來表達自己作為一個年輕人的一種想法,一種爆發。
我記得當時排演一個校園戲劇,也叫實驗戲劇,叫《等待戈多》。那個時候,非常地窮,真的窮得可以說叮噹亂響。一千塊錢演出一個話劇,你們相信嗎?我們這些哥們兒,晚上餓得實在不行了,大家就用一個大鍋來煮速食麵吃。可能石頭喜歡速食麵,就是因為遺傳我這一部分吧。速食麵也沒有什麼營養,然後在裡頭隨便打幾個雞蛋,沒有菜,我們就翻牆出去偷菜,偷完菜回來以後,把外頭的白菜幫子全撕掉,把裡頭的菜心拿手一抓,就放鍋里煮,感覺非常地香,非常地好吃,那是我吃到最好吃最好吃的麵條。
那種經歷雖然很辛苦,但是大家確實是在一種很亢奮的創作狀態里去做事的,當然的確受到了很多人的關注,尤其是很多的女孩子。就覺得你們這些人太厲害了,居然不吃飯還能夠天天排演出這么好的戲,自己感覺到很榮耀,還有很多的滿足感。
大學畢業以後,我又非常順利地跟張藝謀導演、馮小剛導演合作了幾部電影。我的起點很高,所有人都對我敬而仰之,把我當成戲劇學院的一個奇才,我的老師們都說,下面的同學你們看一看,這就是我教出來的學生,他現在怎么怎么樣。那時候我感覺自己在一種不可思議的、莫名其妙的榮耀和自尊心的滿足里生活。
記得當時我住在一個非常小的平房裡,那是我們單位分的宿舍。排隊的那些採訪記者,大概(多到)拐出胡同來,那個時候自己真的有一種很驕傲的感覺,覺得我終於出名了,我終於長大成人、證明自己了。但是到了大概不到三十歲的時候,那個時候的中國電影也是進入到了一個低谷,很多的片子來找我,是我不太滿意的,也是不想接的。
我記得有一次是一九九幾年的時候,我在上海。有一個戲我是(同時)演了一個哥哥和弟弟,是雙胞胎,非常有意思的哥哥在上海灘是白道,弟弟是黑道。兩個人在互相地打,那我白天拍哥哥,晚上拍弟弟,這樣沒完沒了地一直在拍,結果拍到後來,我說,不行導演,我堅持不住了,你讓我休息一下好不好?好吧,晚上回去睡不著覺,自己一個人走在上海的小街道上,沒有任何人,買了一點啤酒,一邊走一邊自己在想,我白天演哥哥,晚上演弟弟,我是誰?那時我真不知道我是誰,我郭濤到哪裡去了,所以當時我的精神狀態,大概就是這樣的,有點找不著自己,有種迷茫的感覺。
可能在座的朋友都不知道我是一個離異家庭的孩子。我記得在我小的時候,(家裡)更多的是爭吵打鬧,我不知道一個正常的家庭生活是什麼樣的,我未來的情感是什麼樣子,非常迷茫,有的時候也很痛苦。我想可能這種迷茫一直延續到我大概二三十歲的時候,我不知道自己的未來,自己的另外一半,自己的很多很多的想法是怎么樣的。可能是因為前面的工作給我帶來的那種榮譽或者是收穫,太迅速,太快了。我在這種迷茫的過程中,好像真的找不到一個途徑,總感覺自己前面是黑黑的一條道,始終往前走,不知道該怎么辦,但是自己不停地一直要努力地往前走。
我記得有一次孟京輝來找我,他想排一個話劇,在1999年的時候,話劇的名字叫《戀愛的犀牛》。我那個時候在開一個酒吧,因為我喜歡喝酒,總是想在那種比較迷茫的時候,用酒精的方式來刺激自己,讓自己睡著,讓自己麻木一點。每天把自己喝得爛醉,暈乎乎地回家,好去忘掉自己在當時的煩惱。我看到孟京輝的時候,我一個人在酒吧的舞台上跳舞,一邊喝著酒,一邊在跳,一個人跳了一個多小時。跳完以後,我滿身是汗,其實更多的是淚水,那個時候孟京輝拍著我的肩膀,他說,XX年新的世紀,馬上就要到來,我們難道不做點什麼嗎?你就想天天這樣去喝酒,天天在這樣一個燈紅酒綠的環境下宣洩自己嗎?你原來對於戲劇、對藝術的追求,到哪裡去了?說得我好像感覺有點毛骨悚然,因為確實我當時的精神狀態和生活狀態都不是太好。我就在想,那么我們排演一個話劇吧。這個話劇我不是為你,也不是為我。也許是在為我的心中的那個人,去較勁,去做一件事情,來證明自己吧。
那個戲,到現在為止對於我來說,其實更多的是一種憤怒,一種宣洩。就像在劇中的馬路,這個人物一樣,女孩子不愛你,你為什麼還要沒完沒了地去追求她,其實就是好像自己跟自己在較勁。新世紀來臨了,一切沒有改變,過去是什麼樣子還是什麼樣子。我說我該怎么辦,下面,還要去再排演一些你自己認為好的東西嗎,還是隨波逐流就這樣走下去?
XX年初的時候,又遇見了我人生當中,非常好的一個哥們兒,那就是寧浩導演,於是乎就出現了《瘋狂的石頭》這部作品。我記得非常清楚,第一次見面交流的時候,他在不斷地跟我講戲,他說哥們兒,你來演這個戲吧,你是我見過最牛的演員,我是看著你戲長大的。說了一個多小時以後,我腦子飛了,我就在想,他跟我說的這個戲,我怎么好像似曾相識啊,這個角色,好像就是為我寫的似的。這對我來說是個機會,你不是就是想要做這樣的戲嗎?你不是就想幹這樣的事情嗎?有這樣一批好哥們兒,大家一塊兒去努力做嘛,自己想飛了,想開了。後來腦子回過神來的時候,導演說大哥,你覺得這戲怎么樣,我說好,但是我沒聽懂,我說不過沒關係,我很喜歡這個戲,我們來一塊兒玩吧,他說好吧,那就一塊兒玩吧。
於是乎我們就開始幹了,那個戲只有三百萬,所有的人不計片酬,每天都在一種非常開心快樂的,非常放得下、放得開的情緒里去創作,跟黃渤、樺哥,我們一起吃火鍋,然後出去蹦迪,喝酒。後半夜說拍你的戲了,直接殺過去拍戲,所有的東西都那么的放鬆、自然、開心,沒有想過任何的外在東西,說我要在這個戲裡,多么的出名,將來我在頒獎禮上要說感謝誰誰誰,從來沒有想過那樣的話,從來沒有想過。
我們自己掏錢租了一個酒吧,動員所有身邊的業內人士說來看這個戲,給我們做做宣傳。那時候感覺,就像是我重新開始起步,從我第一部戲那樣的一個起點開始做起,一點一點地把《瘋狂的石頭》展現給了大家。但是在那個過程當中,我跟我的這幫哥們兒,結下了一生的友情,可以說我現在跟黃渤、跟寧浩我們可以不再見面,我們平時也不打一個電話,但是只要寧浩一個電話,你讓我演一個死屍我都願意,真的。我就是這樣一個人。
關於我情感的歸屬,我一直非常地糾結,也非常地擰巴。直到有一天,我見到了我現在的愛人,她是一個學理工的。這在我過去是絕對不能夠接受的一種人群,因為我是搞藝術的嘛,搞藝術的人一定是(生活)在一種鮮花,浪漫,音樂,掌聲里。而她呢,往往我跟她講,哇怎么怎么怎么樣的時候,我說你能明白嗎,她說你喜歡就好。最有意思的一次經歷就是,我跟我母親的關係雖然很好,但是難免會母子之間會有一些矛盾。有一次我在開車出去的時候呢,我的女朋友在後面,我母親在我的旁邊,我開著車,因為很小的一件事情爭吵起來了。可能因為我們都是搞話劇的,聲音比較響亮,然後跟她越說越激動,而且有點危險,在三環路上。這時候我通過反光鏡,看了一下我老婆,我後來的老婆,她(居然)睡著了。我不知道是怎么樣一個(女孩),好像、也許是老天爺,給予我們的安排,碰到了她這樣一個非常溫柔、體貼的,能夠懂你的心的,而且能夠融化你的這樣一個女孩子,我感到我很幸運,真的。
一個男人的成長有的時候是需要一種精神來寄託的。比方說,你有特別擰巴的時候或者是特別有奮進、有想法的時候,一定要放下架子,放下包袱,努力往前走。但是我不希望大家去較勁,因為我就是一個較勁的人,我用十年給我換來的經驗,在這裡,也許可能對某些跟我同樣經歷的朋友們會有所啟迪,有所幫助。生活不能夠較勁,放下來才能夠走得更長遠,平實的生活才能讓你感受到真實的情感;愛人不一定是非要轟轟烈烈,山盟海誓的,適合你的就好,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