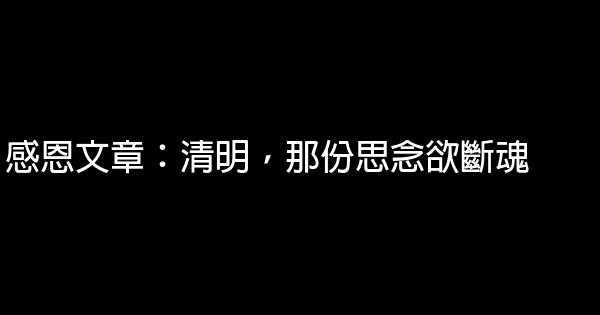又是一年清明節,也是母親去世一周年的祭日,母親已經在青山綠水之間沉睡一年了。
母親是去年的清明之際去世的,帶著她對我們一家人的眷念和乳腺癌病痛的折磨。記得母親去年下葬的時候,一直以來比較晴朗的天空忽然之間飄下了幾滴清明時節的細雨,這次回老家的天氣與那一天是何曾相似,似乎是再一次把刻在我心裡的傷痛雨潤一下,讓那顆種子從此處破土而出,生根發芽。
春雨是太多情了,何須這般殘忍的提醒,這一年來,在我靜下來的時候,無論是睜著雙眼還是睡夢中,母親仍然清晰真切的呈現。
母親自小多難。她兩歲的時候,一個冬天,外公給公社集體放鴨子時,由於鴨群受到驚嚇飛出了窩棚,外公在凜冽的寒風中瑟縮著身體,赤著腳從徹骨的水田裡把鴨群趕到窩棚里後,凍得麻木的的外公蜷縮在野外的火堆旁昏睡了過去,當柴火點燃了臨時的草棚和他的衣服,他也全然不知,外公永遠離開了母親和外婆。
失去了家庭的主要勞動力,在那個年月承受的不僅是生活的拮据,還有來自家庭的排擠苛責。外婆在這種情況下,無奈的帶著母親居住在一座大山下的山溝溝里,幾根簡易的三角木樁支撐下的地方,就是外婆和母親的家。母親後來回憶說:“在那裡,白天晚上都很安靜,聽得最多的就只有狼的叫聲。”後來經人介紹,外婆嫁給了一個從戰場上逃跑的國民黨逃兵,母親和外婆在輾轉中保全了自己的生命。
1959年,母親4歲,那是我們家鄉的過來人永遠都銘刻於心的年月。社會和天氣的因素,那一年家鄉的人們沒米沒糧,很多人就吃樹皮草根,甚至是泥土。外婆手巧,把葛藤的根搗碎做成餅,讓母親得以果腹,延續著生命。後來,母親只要一聽說葛藤,舌頭就立刻反應出乾澀的味道。
生活的多磨鑄就了母親堅韌的個性,也使母親認識到,只有多學一點科學知識,才能走出生活的陰霾。母親沒有讀過書,在我上學的時候,我能從她那裡得到的,就只有這樣樸素的家庭教育觀。正是在這樣樸素的親職教育下,我才懂得生命的可貴。
母親生活一生孤苦,從國中起,我就離家讀書,父親因為要供給我們的學費,常年在外做小工,兩個弟弟甚是頑皮,在感情上不及我體會的深刻,只有我偶爾的回家一次,母親才能和我邊做農活邊說說她的擔憂和希望。母親孤苦,卻不麻木,父親脾氣不好,母親總是能忍受著,我們有三兄弟,她深知父親的肩上的重擔;我畢業工作,娶妻生子,她理解我們工作的繁忙,我孩子十個多月後,她就把孩子帶在老家,一邊幹活一邊照顧孩子;我們三個兄弟,沒有姐妹,她沒有女兒,就把我妻子當做女兒,家裡兩個女人間就有了更多的親密。母親雖不知道“家和萬事興”,但正用自己的奉獻維持著家和。
母親是在2007年查出患了乳腺癌晚期的,手術後一直忍受著病痛的折磨,但是,在病情稍微減輕的時候,她仍然從事著勞動,一直不肯放棄那根拿了幾十年的鋤頭把子,無論我們怎么勸說。2020年的清明之際,母親在劇烈的疼痛中辭我而去,彌留之際的母親無力睜開雙眼,看不見東西,嘴裡卻一直念叨著讓我照顧好父親和兩個弟弟,不停叫著她寵愛著的她的孫子,我的小兒晗。
母親遺體火化那天,我守在靈車中母親的遺體旁,沒有嚎啕大哭,滿腦子都是關於母親的一點一滴,想抓住一點深刻的鐫在自己的內心深處,卻是一片茫然,似乎什麼都印了上去,似乎什麼都牽扯著,還相信母親能在一個我需要她的時刻,能站在我的身邊,但又確切的看見她靜靜的躺在面前,我無奈的只任眼淚隨著撒下的賣路的紙錢,灑了滿地。火化後,按照老家的風俗,骨灰應該放在靈車裡,我決意將母親的骨灰抱在懷裡,母親把我從小背大抱大,在這一刻,我不能讓她躺在冰冷的靈車裡,我要讓母親躺在我的懷裡最後感受她的體溫。
這次回家祭拜母親,甚是匆忙,小兒晗沒有一起回來,我和妻慢慢的踏著老家的青翠蔓草,顯得很安靜,我默默的一路撿拾以前和母親一起走過的腳印,妻默默的承擔著母親留給她的維繫家和的責任。
我想你,母親,您不是以生命存在於兒子的心裡的,兒子從事著科學教育,但我寧願相信有靈魂,我只有以這樣迷信的方式的告訴自己,您在那邊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