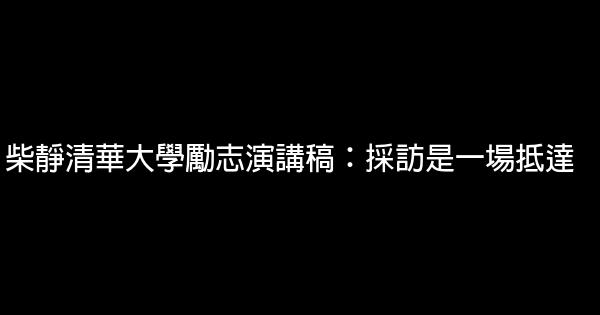沒有夯實的報導,評論只是沙中築塔
我們對於一件事情知道得越少,就越容易形成判斷,而且是越容易形成強烈的單純判斷。
人們頭腦中偏見的根源,往往是來自於無知,我們對於一件事情知道得越少,就越容易形成判斷,而且是越容易形成強烈的單純判斷。
就像我要把一瓶水移動,把它拿到胸前,這是一個很簡單的動作,但是我要把一瓶水非常精確地移動一毫米,這就需要花很多的時間去計算,你肌肉的酸痛度也會增加。
精確是一件需要耗費比較複雜的智力活動的一件事情。報導就要求精確,要求對事實和因果梳理,沒有這個基礎,評論往往就是議論、想像,而不是事實。
我自己在二十三四歲的時候,成為國家電視台的主持人,做一個十六分鐘的新聞深度報導。我覺得這樣的狀況在世界新聞史上也是很少見的,一個年輕人被放到做深度評論的主持人位子上,這是我們剛剛起步的電視新聞決定的一種特殊要求,以後也不會更多地出現。實際上媒體有它的規律,就像一個存在的植物,它必須要按照它的規律生長一樣,要想變得粗壯、強韌,必須到土地裡頭去接受風吹日曬,再一片一片葉子長出來,如果沒有非常夯實的報導作為基礎,那么評論只能是沙中築塔。所以我轉行做了記者,到現在十年了。
採訪是呈現,不是評判
採訪不是用來評判,採訪是用來了解;採訪不是用來改造世界,採訪只是來認識世界。
我覺得對我來說,採訪最大的障礙就是一句話,“我認為我是對的”。這句話看起來不太起眼,但是它造成的障礙會遠遠大於我們的想像,顧準原來說過一句話,他說什麼叫專制,專制就是認為自己絕對不會錯的想法,如果一個採訪者帶著定見,很難了解世界的複雜。
前段時間我採訪魏德聖,他拍的電影《賽德克·巴萊》,就是當年發生在台灣的“霧社事件”,原始部落的人跟日本人之間的一場戰爭。
魏德聖說,在台灣歷史當中關於這個事件只有兩句話,某年某月某日多少人反抗日本軍隊;再看日本的教科書也是兩句話,是某年某月某日台灣某個原始部落的一場暴動。反抗和暴動,這是對於一件事情的兩種解釋。都只有兩句話,都很簡單,但魏德聖說記者式的社會思維要回答的是:“為什麼他們在這個事件中做出了那樣的選擇?”
魏德聖說,他進入這個頭領內心的時候,受過很多的衝擊,一開頭他會熱血激沸,覺得很牛,三百多人就把三千多日本人都幹掉了。但了解越深,他開始發現自己精神上出現了危險的搖晃,比如說他去接觸當年認識這個部落首領莫那魯道的人,那個人跟他講,他根本不是一個英雄,他是一個流氓,每一個經過他部落的人他都會打,他控制欲很強。然後魏德聖又會去想,這個人為什麼會在戰爭之前讓自己的孩子跟家人上吊?有時候他害怕得簡直寫不下去了,因為在不斷地推翻自己的看法,他突破了概念,想要抵達一個真實的人。
一個人進入另一個人心靈的過程是一個可怕的過程,可怕在哪?可怕就在於思想本身,思想本身的危險就在於思想本身是不安的。它拒絕接受已經形成的定見,他需要從自己的思考和感受出發去認識人,這本身就意味著動盪、不安、危險,還有進步。在這個過程當中你會發現你沒有依靠,你原來思想上可能有一個拐杖,但是你不得不把它拋掉,這個拐杖就是人類已經形成的習俗、觀念。就像一個被按在水裡的人,你必須把頭埋在水裡面,學著嗆水才能夠學會思考。
所以我要講的下一句話就是,採訪不是用來評判,採訪是用來了解,採訪不是用來改造世界,採訪只是來認識世界。我很年輕就做了記者,年輕人最熱誠,但是也最容易犯的一個錯誤,就是我們真的想通過報導把這個世界變得更好。
我最初那兩年在公開場合講話或者領獎的時候總是會說,我希望我做這個節目,曾經讓這個世界變得更好。這些話很漂亮吧,聽上去加點音樂就可以上片尾字幕了吧?但是這樣煽情的話並不是職業記者的使命,這個是我慢慢才意識到的。
假如你有這樣強烈改造社會的目的,你就會容易形成你頭腦當中的偏見,你認為世界有一個完美的範式,它就應該向那個方面發展,假如它不是那樣,你就不接受,你就牴觸,你就想改變他,這樣就有兩個後果,一個是你根本改變不了,對方發現你想影響他的時候他就不接受你了,會背道而馳;第二個結果是當你改變不了的時候,就可能因為挫折感或者絕望,放棄了你之前的全部努力。
媒體要提供光亮,照向黑暗未知之處
有同學問,那我們的媒體道德是什麼,我現在認為記者的道德就兩個字,很簡單,就是“明白”:讓人明白,讓人明白這個世界本來面目是怎么樣的,這個就是我們的職業道德。你把這點做好就可以了,即使我不能夠清空自己的一個情緒判斷,也要有一個戒備,佛經中說“念起即覺,覺即不隨”,這個念頭要起來你要能覺察,覺察之後你會不會跟隨它,要有這個意識。
媒體的職責不是提供“熱”而是提供“光”,不需要煽動社會的熱情,媒體是在提供光亮,照向黑暗未知之處。
面對飽受社會爭議的對象,他已經帶著全部的盔甲來面對採訪了,你要感受他,構想如果你是他,這個時候是一個什麼樣的狀態,是一個什麼樣的感受,會做什麼樣的準備。而且,他會因為曾經遭遇過敵意和攻擊,收縮得更為緊張,他時刻做好要么反擊要么逃避。
人在受到威脅的時候只有這樣的模式。
那么採訪要達成的是什麼?採訪達成的是信息,你必須要問輿論期待知道的問題,不可以迴避。但要提供一個讓大家明白這一切造成的因果和背景,那記者就不能夠跟他構成對抗的關係。我現在對自己有一個原則,就是對事苛刻,對人寬容。
大家可以觀察一下我對李永波的這段採訪,很好玩。他說到當年林丹和李宗偉兩個人在上海有過一場比賽,在本土作戰,而且是林丹領先,上海的觀眾就喊了一嗓子“李宗偉加油”,東道主的客氣嘛,林丹一聽連失四球,比賽就輸了。
李永波大發雷霆,在賽後新聞發布會說,這個上海觀眾素質太低了,怎么會這么沒有愛國心,以後我們的比賽都不在上海辦了。我當時採訪羽毛球運動員消極比賽,覺得此事有關他的勝負心,或者對於體育比賽精神和內涵的一個理解,所以我就問他,他一開始是很強硬,他說你怎么可以“給外國人加油”,觀眾怎樣怎樣,結果導致林丹輸了什麼的,我們這樣來往大概有三個回合,他一直很強硬。
後來我把問題稍微變化了一下,意思是說站在一個教練的角度,人們可以理解你會有這樣一種心情,但是在中國羽毛球隊已經發展到這個階段,人們可能會對你有一個更高的期許,就是希望能夠倡導體育文明。他忽然就改變過來說,對,我也覺得,喊“加油”也挺好的,這樣對隊員的心理素質也是一個鍛鍊。
這個改變看起來很突兀,是一個急轉彎,但其實不是,他在面對大量反對聲音的時候,已經在內心去消化和感覺這些聲音了,只是他不願意承認,如果你用敵意的方式去質問,他就會出於防衛把自己的立場踩得像水泥地那樣硬實。
但如果你能理解他何以如此,再把他站立的那個地方松一松,空氣進去了,水進去了,那個土壤變得濕潤了,變得松滑了,他兩個腳站的時候就不會粘固其中,他就會左右搖擺。我剛才說過了,思想的本質是不安,不安就是這種動盪,一個人一旦產生動盪的時候,新的思想就已經產生了,萌芽已經出現了,人們需要的只是給這個萌芽一個剝離掉泥土,讓它露出來的機會。
年輕時期採訪,有時喜歡把對方逼到牆角,攻擊他,反正你手裡也沒有武器了,反正你會倒在地上,那樣更好看。但是人成年了,我覺得還需要某一種寬厚,這個寬厚不是鄉愿,是一種認識,就是你認識到人的頭腦和心靈是流動的,你不要動不動就拿一個大壩把他的心攔起來了,就不讓他進,也不讓他出了,其實人是可以流淌的。
好感和反感是你在觀察人的時候最有害的一種心態,你要在採訪前就對一個人形成了好感或者反感,你就沒有辦法誠實和客觀地觀察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