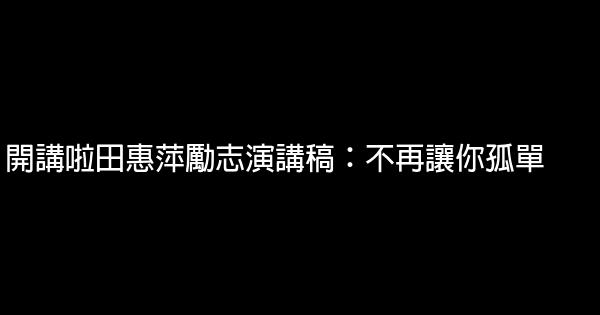其實我是一個大學老師出身,本來講一堂課,在這裡面對著一個時代,花季的最具智慧的一個群體,對我來說,應該是一個家常便飯。但是我今天覺得很緊張,然後我看著你們我忽然剛才走上來的時候,我恍然間又有一種感覺。我想到了20年前,那個時候我作為中國改革開放第一批公派留學生到德國。留學回來以後特別風光,特別風光的站在重慶一所大學的講台上。20多年以前,其實在我一方面享受著大學老師的一種風光的時候,我另外一個方面我的生活開始出現一些變化。
我的兒子他叫楊弢,他是1985年11月1日出生的,他出生5個月,我就出去留學了。他兩歲半的時候我回到他身邊,那個晚上我都記得,我到家的時候是凌晨兩點多坐的火車。我回到家的第二天起來,我的母親這么說,說弢弢跟別的孩子不太一樣,這么說。然後我爸爸就立刻說“沒事兒,他就是說話晚點。”然後我們就坐在那裡,弢弢從那走過去,我爸媽就喊“弢弢,你看,媽媽來了”。他理都不理,就從那個地方往廚房走過去,我媽就說,你看,他就像沒聽見一樣。
所以這個時候是1988年,我就把他帶回了重慶,由我自己去帶他,這一年的時間,到1988年的秋天,這一年的時間是我一生中最艱難的時刻。我必須得承認我的這個孩子和別的孩子,他真的跟別人不一樣,我記得那時候我自己跟我自己說,“田惠萍,你這一輩子都覺得自己跟別人不一樣,但到現在你會發現,能夠活得跟別人一樣,原來是那么奢侈”。我特別特別的害怕。我希望他是一個跟周圍所有的孩子一樣的孩子,哪怕他是一個最普通最普通的人。但是我只要他能說話,只要他能跟別的孩子一樣。這一年當中,我自己的形容就是交織在一種希望、失望、絕望這樣一種情緒當中。我找不到生活的感覺,我每天都在想著有什麼辦法讓我死去,很早我就下了這個決心。如果在我走的時候,我不能看到弢弢有尊嚴,安全,有保障地活著,我就帶他一起走,首先我在死之前,我首先做的事,瀏覽當時我們這一代人,翻譯進來的所有的社會科學哲學方面的書籍,然後我為了尋找人為什麼一定得活著。然後我找了半天,在哲學家這裡找,最後我自己還是給出了一個答案,我的答案是:如果生命繼續存在下去,只意味著被踐踏的話,結束他更人道。我就真的去實施了一次,我把一堆的安眠藥放到粥裡邊。我準備帶著弢弢一起走,我覺得倫理上我已經說服自己了。當然了現在我還活著在這裡跟你們講這個話,說明那個行動肯定沒成功,對不對。但是我著實地跟大家說,我熬了那碗粥之後,全部都是空白,我不知道發生了什麼,我今天都回憶不起來,所以說那個時候我真的是求死不能啊!然後我就對兒子發脾氣,我說因為你,老子連死的權利都沒有。那么對我來說,我明白了一件事,那就是我們只有權利把一個生命帶到這個世界上來,我們絕沒有權利決定這個生命的消失。
從那以後,我的生活態度就發生了一個很大的變化。我的很多朋友都這么說,弢弢,改變了你的人生,弢弢挖掘了你的智慧,弢弢發揮了你的權利,我說是弢弢讓我活得幸福,讓我活得明白!那么我就知道了:所有以前附在我身上的我自己以為值得我去驕傲,值得我去自豪,值得我去怎么樣的得意的那些東西其實都是那么的表面,我發現其實拷問你最後自尊尊嚴和你驕傲的支撐的這些東西是你能否擔當得起責任。
1992年的國慶節10月份,我帶著孩子到北京,我想最後嘗試一下,醫學還能做些什麼。那么到了北京以後,當時的全中國,我後來才知道,只有三個半醫生能開具自閉症的診斷書。當時我跟醫生說,“如果我要有條件,我就辦這樣一個學校,我把這些孩子都領到我身邊。”然後當時醫生看著我的雄心壯志,忍不住給我潑個冷水,他說,“田惠萍你做不完,全中國有50萬呢!”
在1992年,1993年的時候,世界上關於自閉症的發病率是萬分之四到萬分之五,而今天,我們去年11月份,從美國回來,在加利福尼亞州他們給我們的是100個人裡邊有8個,就是這個發病率。我一聽這個數字,如果田惠萍還真有什麼不一樣,大概就在這種時候,我就會蹦出來,我說“你要跟我說,全中國就40個,那就拉到吧,我帶著孩子回家認命吧。但是如果你跟我說中國有40萬,我覺得這就是一件值得去做的事。”
當時還真激勵了我,我唯一一個就是,我要跟我這個大學老師這個職業說再見有點遺憾。因為我覺得,那是一個我那么喜歡的職業,但是義無反顧。
1993年2月12日凌晨2點40分,火車因為晚點,進北京站就是這個時間。我在北京站看到北京所有建築物都是個剪影。那一瞬間我有一點膽怯,我說“田惠萍你是不是有點太大膽了!”我說實話,多年後很多人問我那時候你有什麼條件來創業,我說我就是一個旅行包,旅行包里我所帶的兩樣東西,一個是換洗衣服,一個是我內心的想法,我要做一件事,這件事我要告訴社會,有這樣一個群體,他們有孤獨症,他們有自閉症,就帶這樣兩個我來到北京。
1993年3月15日,第一批6個孩子,真的招進來了,招進來了。開學的第一天,我們有6個孩子,全都嚇壞了。我在北京西城區招了4個老師,當我們走進去的時候,這6個孩子我形容叫“海陸空”。什麼意思呢?床底下鑽的有,床上跳的有,窗台上站的也有,招來的這4個幼師是普通的老師,都被嚇壞了。那個鞋掉了,那個拉了大便以後自己拖著大便在跑。我能回想起來,我累得……我盯了三天三夜,後來那天他們說,田老師你去睡一會吧,後來那天他們說,你這一躺下就沒氣了,他們說我們都過去摸你的鼻子,你是不是真的死了,就說因為我累得就累成那樣。
我是一個單親媽媽,帶著弢弢在北京,一方面辦著“星星雨”。那么我要是每天都要接送他去學校的話,我真的是什麼都不用幹了。因為我每天從我租的房子到“星星雨”去,來迴路上是4個小時的公共汽車,所以我根本是不可能兼顧。最後我想不行,我就試試看弢弢能不能夠上學,我發現他不認識車牌,所以我就帶著他到公交總站去,說“弢弢這是幾路車”,讓他去摸這個車牌。“5路,哎呀,弢弢真棒!”任何一個車,那是27路,那是54路,那是多少路……直到弢弢都能認出來,再站到我們那個車站上。然後那天弢弢又到了,我和弢弢如往常一樣,我就看他在後面已經站在門口背著書包這樣站著,我從心裏面說,我說“弢弢真棒!”結果發生一個事情,就是這個車,北京那么長個公共汽車一共三個門,他前面兩個開了,關上,車啟動走了,我們弢弢站的那個後門沒開。我就跟過去,我就衝過去拍那個車門,我嗓門本來就大,你知道我就這么喊,我楞喊前面那個司機停車了,不等售票員說話。那售票員就說有人下車嗎,我說後門有人下,你開門,他一開門,我們弢弢就下去了。那個售票員氣不打一處來,“我問了他了,我問了他那么多聲了,他都不回答,他怎么不答應?”我當時就衝過去,我就跟售票員說,我說“我只想跟你說,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回答問題!”車接著開走了。一車的人都用異樣的眼光看我。所以在家的時候我得練,於是我就模擬北京售票員說話(……)然後叫弢弢回答下車,知道吧。他在三年級下半學期,就完全自己背著書包自己上學放學了。所以我想說,每當我今天路過這種普通國小在下午放學時期門口,我看著那么多的家長,我的媽呀,我就在想,看我們家弢弢多能幹!
XX年的8月份,在北京東郊的村莊裡面,也就是“星星雨”現在所在的地方,我是做最後一次工作匯報。因為從下個學期開始我就退休了。這個事情我覺得是我人生最驕傲的一次,而且因為我們這個團隊的工作,我們帶動了中國從特殊教育到中國的立法、法律上對自閉症人的關注。中國隨著這種新媒體社會監督這樣的能力的增強,拷問中國的民間公益組織、慈善組織的財務那么多,但是你想想20年的“星星雨”我們從來都沒有被質疑過,難道我們不該為此感到驕傲嗎?
人有多皮實,你怎么想像都不過分。所以我就覺得回顧我的一生,我有過高峰, 有過低谷,在別人的眼裡我可以很悲慘過。但是今天我想說,我跟大家說每一種人生他的路上都有獨特的風景線,每一種人生都是精彩的。不管你們這一代人面對的社會有什麼樣獨特的挑戰,相信自己,走你自己的路,過自己的人生,你們也是改變時代的一代人。
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