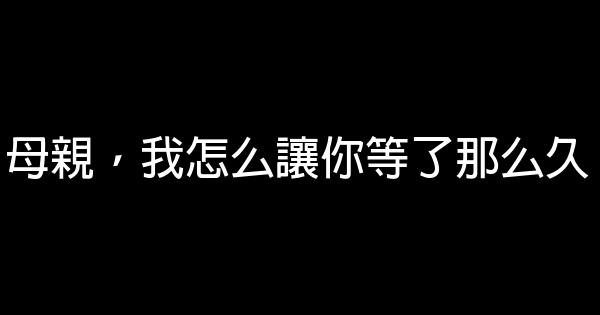母親真的老了,變得孩子般纏人,每次打電話來,總是滿懷熱忱地問:你什麼時候回家?且不說相隔一千多里路,要轉三次車,光是工作、孩子已經讓我分身無術,哪裡還抽得出時間回家。母親的耳朵不好,我解釋了半天,她仍舊熱切地問:你什麼時候能回來?幾次三番,我終於沒有了耐心,在電話里大聲嚷嚷,她終於聽明白,默默掛了電話。隔幾天,母親又問同樣的問題,只是那語調怯怯地,沒有了底氣。像個不甘心的孩子,明知問了也是白問,可就是忍不住。我心一軟,沉吟了一下。
母親見我沒有煩,立刻開心起來。她欣喜地向我描述:後院的石榴都開花了,西瓜快熟了,你回來吧。我為難地說:那么忙,怎么能請得上假呢!她急急地說:你就說媽媽得了癌,只有半年的活頭了!我立刻責怪她胡說,她呵呵地笑了。小時候,每逢颳風下雨,我不想去上學,便裝肚子疼,被母親識破,挨了一頓好罵。現在老了,她反而教著女兒說謊了,我又好氣又好笑。這樣的問答不停地重複著,我終於不忍心,告訴她下個月一定回去,母親竟高興得哽咽起來。
可不知怎么了,永遠都有忙不完的事,每件事都比回家重要,最後,到底沒能回去。電話那頭的母親,仿佛沒有力氣再說一個字,我滿懷內疚:媽,生氣了吧?母親這一回聽真了,她連忙說:孩子,我沒有生你的氣,我知道你忙。可是沒幾天,母親的電話催得越發緊了。她說,葡萄熟了,梨熟了,快回來吃吧。我說,有什麼稀罕,這裡滿街都是,花個十元八元就能吃個夠。母親不高興了,我又耐下性子來哄她:不過,那些東西都是化肥和農藥餵大的,哪有你種的好呢。母親得意地笑起來。
星期六那天,氣溫特別高,我不敢出門,開了空調在家裡待著。孩子嚷嚷雪糕沒了,我只好下樓去買。在暑氣蒸熏的街頭,我忽然就看見了母親的身影。看樣子她剛下車,胳膊上挎著個籃子,背上背著沉甸甸的袋子,她彎著腰,左躲右閃著,怕別人碰了她的東西。在擁擠的人流里,母親每走一步都很吃力。我大聲地叫她,她急急抬起滿是熱汗的臉,四處尋找,看見我走過來,竟驚喜地說不出話來。一回到家,母親就喜滋滋地往外捧那些東西。她的手青筋暴露,十指上都裹著膠布,手背上有結了痂的血口子。母親笑著對我說:吃呀,你快吃呀,這全是我挑出來的。我這沒有出過遠門的母親,只為著我的一句話,便千里迢迢地趕了來。她坐的是最便宜、沒有空調的客車,車上又熱又擠,但那些水靈靈的葡萄和梨子都完好無損。我想像不出,她一路上是如何過來的,我只知道,在這世上,凡有母親的地方就有奇蹟。母親只住了三天,她說我太辛苦,起早貪黑地上班,還要照顧孩子,她干著急卻幫不上忙。
廚房設施,她一樣也不敢碰,生怕弄壞了。她自己悄悄去訂了票,又悄悄地一個人走。才回去一星期,母親又說想我了,不住地催我回家。我苦笑:媽,你再耐心一些吧!第二天,我接到姨媽的電話:你媽媽病了,你快回來吧。我急得眼前發黑,淚眼婆娑地奔到車站,趕上了末班車。一路上,我心裡默默祈禱。
我希望這是母親騙我的,我希望她好好的。我願意聽她的嘮叨,願意吃光她給我做的所有飯菜,願意經常抽空來看她。
此時,我才知道,人活到八十歲也是需要母親的。車子終於到了村口,母親小跑著過來,滿臉的笑。我抱住她,又想哭又想笑,責怪道:你說什麼不好,說自己有病,虧你想得出!
受了責備的母親,仍然無限地歡喜,她只是想看到我。
母親樂呵呵地忙進忙出,擺了一桌子好吃的東西,等著我的誇獎。我毫不留情地批評:紅豆粥煮糊了;水煎包子的皮太厚;滷肉味道太鹹。母親的笑容頓時變得尷尬,她無奈地搔著頭。我心裡暗暗地笑,我知道,一旦我說什麼東西好吃,母親非得逼我吃一大堆,走的時候還要帶上。就這樣,我被她餵得肥肥白白,怎么都瘦不下去。而且,不貶低她,我怎么有機會占領灶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