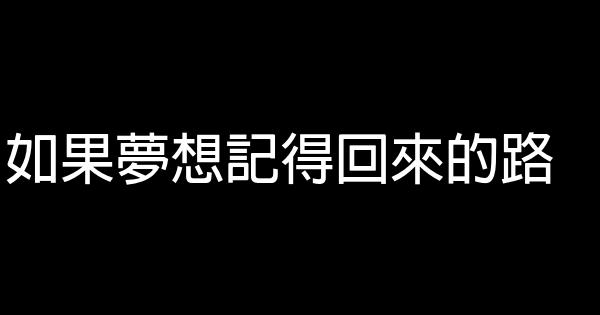文/楊清媛
我一直都記得。
那時我們都說要去很遠的地方。
而我們在那段被稱之為“時過境遷”的時光里,又留下些什麼來丈量年輕的寬度呢?
是夢想。
總有一天,它要以翠綠的形式回歸地面。
當時,還未明白蒼白的現實究竟以怎樣的姿態掌控著生命的脈搏,於是用愈加直白的方式抬頭仰望這個世界,素麵朝天。
小時候,當被老師問及“長大後想當什麼”一類因重複多次而略顯俗套的問題時,還是會很認真地思考一番,然後歪歪扭扭地在紙片上寫下諸如“歌星”“科學家”“企業家”等等正統而光芒萬丈的名詞。顯然,完全忘了考慮是否具有實踐性。然後得意洋洋地伸頭去看鄰座夥伴寫的是什麼,互相比較一番。在略微懊惱自己寫得不如別人稱心後,便大大咧咧地扯開了話題。所謂理想,便是不了了之。以至於一星期後再回憶那天紙片上所寫的文字時,腦海里唯一的印象便是一大片荒蕪的墨漬。
吶,自然不懂得落筆的重量,這一筆盪開,仿佛未來都在觸手可及的地方靜靜地等待綻放。墨香不退,星芒不散。
其實,很久以後的今天,除了喟嘆年少時候太驕縱,更多地,還是懷念那些用浪漫的情懷來接納未來的我們。
深深地緬懷。
杜牧曾賦一首《嘆花》給一位愛而未得的女子:“自恨尋芳到已遲,往年曾見未開時。如今風擺花狼藉,綠葉成陰子滿枝。”
當韶華揮霍殆盡,轉而尋覓當年巧笑嫣然的你,卻自知已是遲了。曾經初見你的時候,你還沒有長大,美好得像枝頭的花兒。如今再回首,你已是晚風裡飄搖的殘花。綠葉成了蔭,果實滿了枝。可惜都不是關於我的。
對於我們,可否將這女子看作我們的夢想。曾經,她在年輕的光陰里肆意地燦爛,而我們卻不懂得珍惜,當多年後懊悔地回憶起來,這夢想已經不屬於自己了。
令人欣喜的是,早年也有立志當一位詩人的目標,並持續了一段較長的歲月。鍾愛於長長短短的詩句,鍾愛於詩里更富有張力的文字。
會攢下一星期的零花錢,在別人舔冰激凌的時候,我會加快腳步地離開,偷偷地咽下口水。只為了去買一本精緻的本子。然後一筆一畫地寫下自己的詩。滿心歡喜。
還記得本子的封面很好看,背景是一大片安靜的熏衣草,一個穿著百褶裙的女孩被碩大的熱氣球拉得飄了起來,笑靨如花。
像極了某個姑娘。
原以為夢想可以預見,在漫長而蜿蜒的盡頭等我。
再也沒有荊棘。
可惜成長注定是緩慢而殘酷的。曾經那個關於詩人的、小小的夢,在繁重的學業前是那么卑微。夢想成了“志願”、成了“大學”、成了“分數”。我們都不可免俗地追逐著這些,在年復一年的日子裡,忘記了如何去波瀾壯闊。
一些人,一些事,一些情懷,一些夢想,失了顏色,失了重量。
我聽見有寂寞靜靜地滴落下來。
偶爾會在安靜的晚自修上淡淡地出神,桌上攤開的數學題典讓人禁不住皺眉,如果有人抬頭,一定會看見我臉上惆悵的情緒吧。可是直到如今,依然沒有人發現過。
至於那本詩集,如今正躺在我的床櫃裡,許久沒有翻動過了。一些很美麗,很美麗的句子還是一如既往地美麗。
席慕容有句詩是這樣的:“在黑暗的河流上被你遺落了的一切,終於只能成為星空下被人靜靜傳誦著的,你的昔日我的昨夜。”
夢想就像我所珍愛的人。是啊,你的昔日我的昨夜。
夢想是一生的信仰,它會停歇,它會轉彎,它會悄悄沉默下來,可它一直都在。
也許我們因為種種,將它遺忘在泛黃的過去。別擔心,它會記得回來的路。
我們已經長大,所以,一定要找回它,免它驚,免它擾,免它四下流離。
為了夢想,一定要風雨兼程。記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