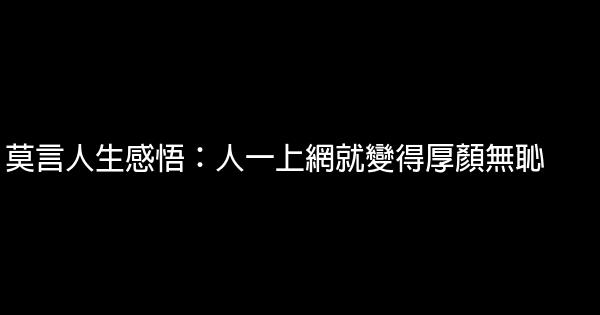網路是個被文人雅士吹唬得神乎其神的地方,也是個被同樣的文人雅士貶斥得一文不值的地方。至於我個人,對於自己不懂或是不太懂的事物,總是出言謹慎,不敢輕易臧否。去年被人強拉去給網上文學做了一次評審,結果惹得網上精英們很不高興,說既不上網又不在網上發表文章的人如何能有資格當網上文學的評審?精英們的批評讓我感到口服心服,既不上網又不能在網上發表文章的人的確沒有資格當網上文學的評審,就像既不欣賞音樂又不能創作音樂的人沒有資格去給音樂比賽當評審一樣。
自我檢討之後,一種強烈的自卑感油然而生。“90年代不上網,就像70年代不入黨。”這比喻聽起來很順耳,但並不貼切。70年代要入黨,除了自己表現積極,服從領導、團結同志之外,關鍵還要家庭出身好,家庭出身不好,表現得再積極也是白搭,弄不好還會給你戴上一頂“偽裝進步”的大帽子。而90年代的上網,只要家裡有台電腦、有根電話線,隨時都可以上,一不要寫申請,二不要什麼人批准,更不需積極表現。但我為什麼遲遲不上網呢?因為我對涉及到機械、電子之類的東西心懷恐懼,總認為這些東西高深無比,非有天才學不會。後來我坐計程車,與司機閒談起來。司機說,上網比上床還要容易,上床前你還要洗腳刷牙脫衣服,上網前什麼都不需要。他還說,開車比上網還要容易。我問他像我這樣的人用一個月的工夫能不能學會開車?他說:別說是您,把一頭豬綁在駕駛盤前一個月,它也會了。
在這個司機的鼓勵下,我終於上了網。上網之後發現,所謂網上文學跟網下的文學其實也沒有什麼根本的區別。如果硬要找出一些區別,那就是:網上的文學比網下的文學,更加隨意、更加大膽,換言之,就是更加可以胡說八道。一個能在紙上寫作的人,只要不吝惜電話費和網路費,完全可以在網上寫作。唱歌跳舞你不會,胡說八道難道還不會嗎?漸漸地我也知道,大多數的網上文學,都是在網下寫瞭然後貼上去的。因為寫作時就知道了要往網上貼,所以這在網下創作的東西,也就具有了網上文學胡說八道也可以叫做“語不驚人死不休”的素質。有了這些經驗之後,所以當網站讓我開一個專欄時,我稍微猶豫了一下就答應了。今後,我也可以大言不慚地說:我也是個網路寫作者,我已經取得了給網路文學當評審的資格了。為了證明網下的寫作與網上的寫作差不多,現在我就把我幾年前為自己的散文隨筆集《會唱歌的牆》寫的序貼上來:這是我的第一本散文、隨筆集,但我更願意說這是一盤羊雜碎。我拿不準收集在一起的這些文章究竟是散文是雜文是隨筆還是別的什麼鳥玩意兒。想不到這十幾年來,除了小說和劇本之外,我還寫了這么多胡言亂語。前幾年散文、隨筆熱門時,前後大約有十幾家出版社動員我編一本集子,我心裡虛得很,不敢應承。因為我想一個人寫小說時總是要裝模作樣或是裝神弄鬼,讀者不大容易從小說中看到作者的真面貌。但這種或者叫散文或者叫隨筆或者叫雜文的雞零狗碎的小文章,作者寫作時往往忘了掩飾,所以就更容易暴露了作者的真面孔。如果是貌比潘安,暴露了正是一件幸事;如果是貌比莫言,暴露了豈不麻煩?人貴有自知之明,我有自知之明。據說寫散文、隨筆要有思想,我沒有思想,有的只是一些粗俗的胡思亂想;據說寫散文、隨筆要有學問,我沒有學問,有的只是一些道聽途說的野語村言;據說寫散文要有高尚的情操和美好的理想,這兩樣東西我都沒有,有的只是草民的念頭和生理性的感受,所以我輕易不敢把這些東西集中起來示眾。那么為什麼又把它們收集了起來呢?第一個原因當然是因為版稅,第二個原因嘛,我想既然說百花齊放那就應該讓狗尾巴花也放,既然要百家爭鳴就允許讓烏鴉也鳴。就像我的存在使一直嘲笑我相貌醜陋的那些貌比潘安的男作家更潘安一樣,我的散文、隨筆集的出版,也會使中國的散文隨筆集們深刻的顯得更深刻,淵博的顯得更淵博,高尚的顯得更高尚,美好的顯得更美好。
這不過是我的夢想而已,其實在這個年代裡,多一本書或是少一本書,就像菜市上多一棵白菜還是少一棵白菜一樣,甚至還不如。寫完這自序之後,我就開始修正文中的觀點。一個人在寫小說時裝模作樣、裝神弄鬼,寫散文、隨筆時何嘗不是裝模作樣、裝神弄鬼呢?小說是虛構的作品,開宗明義就告訴讀者:這是編的。散文、隨筆是虛偽的作品,開宗明義告訴讀者:這是我的親身經歷!這是真實的歷史!這是真實的感情!其實也是編的。一個愛好嫖娼的男人,偏偏喜歡寫一些讚美妻子的文章。一個在海外混得很慘的人,可以大寫自己在美國的輝煌經歷,可以寫自家的游泳池和後花園,可以寫自己被柯林頓請到白宮裡去喝葡萄酒,希拉蕊還送給他一件花邊內衣。一個連鄧小平騎的那匹騾子都沒見過的人,在鄧小平去世之後,就可以堂而皇之地寫回憶文章,回憶在大別山的一條河溝里,自己與敬愛的鄧政委在一起洗澡的情景。一個自己的爹明明只是一個團副的人,在散文、隨筆里,就可以把自己的爹不斷地提升,一直提升到兵團副司令的高位。吹吧,反正不會有人去查你爹的檔案。一個在成為作家之前明明只是個醫院勤雜工的人,在成了作家之後,在散文隨筆里,就先把自己提拔成護士長,然後提拔成主治醫生,最近已經把自己提拔成了給葉爾欽總統做過心臟搭橋手術的主刀大夫了。下一篇散文就可以寫寫你給毛澤東主席做白內障手術的事了。你想讓讀者知道,你當作家是在客串,是很不情願的,你的最大的才能是表現在醫學方面。受你的啟發,我準備寫一篇回憶文章,回憶我少年時參加全地球鋤地比賽的情景,那是1960年,我五歲,比賽的地點在北大荒,評審有王震將軍,有朝鮮的金日成首相,還有越南的胡志明伯伯。比賽開始前,胡伯伯摸著俺的頭說:好孩子,好好鋤。得了冠軍獎給你一個大豆包!一個明明連《三國志》都讀不通的人,照樣可以引經據典地寫“學術性”的歷史文化散文,資料不夠,大膽編造就是,越是沒影兒的事兒越是安全。你說蘇東坡中過狀元那是不行的,但你說蘇東坡在海南島嫖娼誰也挑不出你的毛病。你說托爾斯泰來過你的老家是不行的,但如果你說,你的老爺爺曾經到過俄羅斯,在一個小酒館裡跟托爺爺碰過酒盅子那是可以的。你點名道姓地說一個上海的著名評論家把你譽為比魯迅還要深刻、比徐志摩還要浪漫、比錢鍾書還要博學的偉大文學家那是不行的,但是你說模里西斯的一個著名的評論家這樣評價你是可以的。
前幾年有人還批評人家台灣的三毛,說她的那些關於大沙漠的散文是胡編的。我覺得這些人真是迂腐,誰告訴你散文、隨筆都是真的?你回頭看看幾十年來咱們那些著名的散文、隨筆,有幾篇是真的?大傢伙兒都心照不宣地胡編了幾十年了,為什麼不許人家三毛胡編?
咱家也坦率地承認,咱家那些散文隨筆基本上也是編的。咱家從來沒去過什麼俄羅斯,但咱家硬寫了兩篇長達萬言的俄羅斯散記,咱家寫俄羅斯草原,寫俄羅斯邊城,寫俄羅斯少女,寫俄羅斯奶牛,寫俄羅斯電影院裡放映中國的《地道戰》,寫俄羅斯小販在自由市場上倒賣微型核子彈。咱家的經驗是,越是沒影的事,越是容易寫得繪聲繪色。寫時你千萬別心虛,你要想到,越是那些所謂的散文、隨筆大師的作品,越是他娘的胡扯大膽,天下的巧事兒怎么可能都讓他碰到了呢?如果你經常地翻翻那本十分暢銷的《讀者文摘》,你就會明白,那些感人至深的寫”親身經歷“的文章,其實都是克隆文。
還有那些“訪談錄”、“自傳”、“傳記”、“日記”,我勸大家都把它們當成三流小說來讀,誰如果拿它們當了真,誰就上了作者的當。
短短的上網經驗使我體會到,人一上網,馬上就變得厚顏無恥,馬上就變得膽大包天。我之所以答應在網上開專欄,就是要藉助網路厚顏無恥地吹捧自己,就是要藉助網路膽大包天地批評別人。當然我也知道,下了網後,這些吹捧和批評就會像屁一樣消散——連屁都不如。當然我也知道,上網的人裡邊確實也有很多品德高尚、思想健康、表里一致的人,但“歪船野馬偏激文章”,如果此文傷害了誰,就請放開喉嚨罵一聲:呸,這算什麼狗屁文章!舊“創作談”批判1984年秋,初入解放軍藝術學院,曾經寫過一篇有關創作的短文:天馬行空。
作家在進入創作過程之前和創作過程中,最艱苦也最幸福、最簡單也最複雜的勞動就是想像。沒有想像就沒有文學。沒有想像的文學就像摘除了大腦半球的狗,雖然活著但是沒有靈氣,雖然活著也是一條廢狗。因此雖然沒有想像力的文學作品雖然不缺”零件“但缺少最重要的靈氣,所以也不能算真正的文學作品。生活是創作的唯一源泉,這無疑是正確的,但僅有生活還是不夠的,因為人人都在生活,但並不是人人都能寫作。寫作的人當中不少也是在湊熱鬧,寫不出真正意義的文學作品,他們的問題就是缺少天才和靈氣。一個文學家的天才和靈氣,集中地表現在他的想像能力上。浮想聯翩,類似精神錯亂,把風馬牛不相及的若干事物聯繫在一起,熔為一爐,燴成一鍋,糅成一團,剪不斷,撕不爛,扯著尾巴頭動彈,這就是想像的簡單公式和一般目的。
作家在進入想像過程之後,必須藉助於想像給原始的生活素材插上飛動的翅膀。能飛起來的當然好,飛不起來的正是要淘汰的菜鳥。這種想像也是對原始素材的加工和蒸餾,升華和提高。只有經過了想像的東西才是非常靈動、非常活潑、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東西,否則就會僵化、老化、固定化、程式化。
要想搞創作,就要敢於衝破舊框框的束縛,最大限度地進行新的探索,猶如猛虎下山、蛟龍入海,猶如國慶節一下子放出了十萬隻鴿子,猶如孫悟空在鐵扇公主肚子裡拳打腳踢翻跟頭,折騰個天昏地暗日月無光一佛出世二佛涅槃口吐蓮花頭罩金光手揮五弦目送驚鴻穿雲裂石倒海翻江蠍子窩裡捅一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