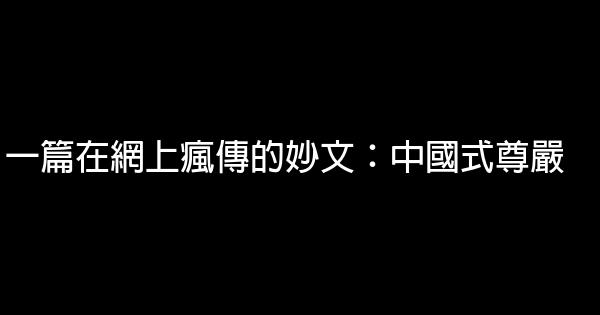文/艾約
一個大學同學,畢業後五年在二十八歲時就任近十萬人口縣屬小鎮鎮長。三年後升任為該縣宣傳部長,而後副縣長,配有專車和專門的司機。他的政治野心不小,在官場上如魚得水。有一年回國我去看他,他開口的第一個問題就是;你為什麼不回國?中國應該有更適合你的專業的位置和機會。
我想都沒有想地答道:為了有尊嚴地活著。
同學十分不解地看了我一會兒。但他沒有繼續追問,而是讓他的司機隨時待命,親自開車帶我去他工作和管轄的地區轉轉,並開玩笑說:好多年我都不開車了,但是今天,我給你當司機!我明白他的意思今天我是他的貴賓,但經他這么有意一說,也讓我意識到他今天在降尊紆貴。司機,在他眼裡是低人一等的僕從。
我們每到一處,總是被一群人圍著前恭後迎,小心賠笑奉承有加,連到餐館吃飯都是老闆親自出馬,殷勤備至。我跟著他狐假虎威了一回,體驗到有如皇帝出遊般前呼後擁的至尊至貴,這是我在美國沒有的經歷。
飯後同學舊話重提,吹捧說我在中國肯定會混得比他好,為什麼會有在中國活得沒有尊嚴的想法呢?我沒有回答他的問題,而是問他,如果某一天他成為一介平民的話,他還會有這樣每到一處的禮遇嗎?他說他沒有想過自己將來會成為一介平民,但如果是的話,估計不會被人這樣奉迎著。這就是了。其實在中國沒有必要成為一介平民來體會尊嚴的差別,只需換個角度,你能不能像尊重你的上級一樣來尊重你的司機?他們只不過是職業的不同而已。同學老實承認不能,也突然明白我的意思,感嘆道,儘管他在這兒人模人樣,但如果去省城或北京的話,肯定也是一條哈巴狗,甚至被人當成流浪狗。
沒錯,在中國,一個人是否被尊重和被尊重的多少取決於你身上披著的社會身份的大小或財富的多少。
在美國,我是典型的一介平民,儘管操著不太流利而且有口音的英語,以及長著不主流的面孔,但每到一處我很少有不被尊重的感覺,僅有的幾次還是來源於自己的同胞和新移民。無論是學習工作場所,還是生活消費場所,無論是錦衣繡服,還是破衣濫衫,我個人的經歷還沒有被人公開歧視過。但在中國,我卻時時處處感到不被尊重和歧視,或因為不太高檔的衣著,或因不太主流或優越的口音,或長得不富或不貴的面孔等等。說人家美國人是表里不一的偽君子也好,假仁假義的偽善者也好,但人家至少文明到不會明目張胆地歧視人或輕賤人甚至羞辱人。
我也告訴同學,我每天很驕傲地給自己和家人當司機,有時候也給同事和朋友當司機。工作午餐外出就餐時,經常是老闆或老闆的老闆給我們當司機。我所在的美國的城市市長,甚至多數國務部長、國會議員或州長都是自己開私車上下班。即使雇用司機也會對他們彬彬有禮,因為一方面對人本身的尊重是西方的基本價值,另一方面司機手裡握有這些人的一票。
像有權的同學一樣,一個有錢的同學也不太明白尊嚴在中國是個問題。在中國的經濟和司法還隨處有縫可鑽的時候,這個同學憑藉在政府部門的特殊關係,在只賺不虧的房地產行業找到了他成為富人的位置;在中國的道德開始墮落到以更新妻子包養二奶為榮的時候,他不僅與時俱進地換了個年輕漂亮的妻子,而且在同學朋友中從來不隱瞞包養的情人。現在他家裡僱傭了兩個保姆和一個專職司機,這些也是他向人展示他的財產的一部分。總之,他總是踩著了時代的步伐,以至他時常感嘆,生為男人,只有生在中國才值得。如此的際遇,尊嚴在他那兒當然不是問題。
“尊嚴”的話題被提起也是因為他不理解我為什麼不回國,是在一幫老同學聚會上,這個有錢的同學在一家餐館請客。到了該點菜的時候,有錢的同學一招手,四個服務員同時快步躬身迎上來。那是個特殊的包間,配有四個服務員站在房間四角隨時待命。同學嫌他們有礙同學間的私密話題把他們趕到了門外。每次有要求,他只需要一招手或對外高聲叫道:服務員,再拿份選單!服務員,飲料!服務員,點菸!等等。點菜的口氣更是鏗鏘有力。當他再次埋頭揮手招人時,沒有注意到身後一個服務員手裡拿了一杯酒正準備遞給他,結果酒杯被打落在地,一些酒灑在他身上。同學大眼一瞪,服務員嚇得面如灰色連連道歉。我坐在一旁,津津有味地“欣賞”著同學那高高在上有如指揮千軍萬馬的氣勢,想像不了這曾經是個見了女生就滿臉通紅、以至初戀情人被人搶走後無助地失聲痛哭的大男孩。金錢,是如此地能把一個懦夫變成強者和尊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