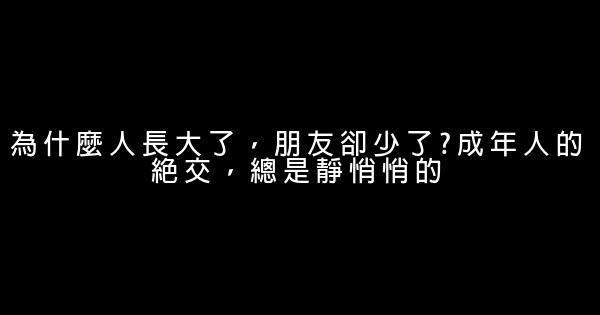散場是多數友誼的最終走向。
《重慶森林》裡有句話是這樣說的:
「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在什麼東西上面都有個日期。
秋刀魚會過期,肉罐頭會過期,連保鮮紙都會過期。」
然而我沒想到,友誼其實也會過期。
意識到這點時,我正在參加一場高中同學的婚禮。
說是婚禮,更像聚會,仔細想想,自從高中畢業,
我們一群人已經6年多的時間沒見過面了。
這其中,就有一個當年很要好的朋友。
那時他睡在我上鋪,又是我的同桌,加上有很多共同愛好,關係一直很鐵。
平常時候我們幾乎無話不聊,從愛好到各種八卦傳聞,能從早聊到晚。
每逢週末,不是去他家玩,就是到我家玩,偶爾有個週末我媽不見他都會感到奇怪。
每個週五晚,都會買上幾罐啤酒,爬到宿舍樓頂,就著酒驅散年少心事,
直到三更半夜才溜回去睡覺。
那段日子裡,我們之間要好的程度讓我真的覺得,友誼會地久天長。
少年還是不識愁滋味,後來的一切卻事與願違。
時間往後推,我們畢了業,友誼也好像畢了業。
我們考上了不同的大學,雖然相隔很遠,
但一開始還是會彼此聯繫,分享著自己身邊的事情。
只不過不知怎的,聯繫變得刻意,從談天說地變成只問候在幹嘛,
一整年下來幾乎沒見過面,慢慢聯繫變得越來越少。
後來,兩人都很有默契,斷了聯繫。
那天同學婚禮結束後,我和他在微信上寒暄了幾句有的沒的,
再找不到以前聊天的感覺,也不知道聊啥,
便像從前一樣,安安靜靜躺在對方的通訊錄裡。
我問過身邊好些人,每個人都會有那麼幾個曾經很好,如今失聯的朋友。
幾乎所有人都不知道,什麼時候就落下了這份友情,很多人都是後知後覺。
我有一個前同事,早些年前,她有個形影不離的閨蜜,
也是無話不聊,彼此都知道對方很多心事,每天的聊天記錄都是滿滿噹噹。
但這些都在她去了另一座城市工作後,悄然發生了變化。
因為兩人工作都忙,沒什麼時間聯繫對方,
加之後來都有了新的圈子,就徹底斷開了聯繫好幾年。
原本以為就這樣彼此再不會有所交集,沒曾想某天閨蜜打破了彼此的安靜。
靠的是一條砍價信息。
藉由那次,彼此客套了一番,沒聊上幾句便消失了。
之後也有過幾次的聯繫,只不過都是砍價、點贊、投票等等消息。
一開始前同事還會幫忙,可一次又一次,以前那份情誼慢慢被磨滅乾淨,後來索性懶得幫忙了。
對比起那些因為吵架而走散的友誼,這樣的友誼收場方式更為常見。
即便刻意維繫,也是在打破打破現有的平衡,多數時候都是適得其反,弄得彼此尷尬。
所謂相見不如懷念,大抵就是如此。
我問過身邊好些人,每個人都會有那麼幾個曾經很好,如今失聯的朋友。
要說最理想的友情,應該是像高曉松和老狼那樣。
當年高曉鬆在清華組建樂隊時,認識了老狼。
此後高曉松負責寫,老狼負責唱,兩人十分默契,相處中兩人關係也變得十分要好。
好到有年暑假樂隊被請去海口一家餐廳駐唱,錢很少,沒人願意去,只有老狼陪著高曉松去。
那時的住宿條件很惡劣,他們被安排與服務員們打地舖,
大夏天還沒空調,熱得人難受,可老狼沒有怨言。
而高曉松沒了錢,不回家了,兜兜轉轉當起了流浪歌手。
畢業時間很快來臨,老狼給人裝起了電機,退學的高曉松已經暴富。
那時高曉松依舊在為老狼的生計憂愁,寫的歌都一定要讓他來唱,以此幫助窘迫的老狼。
老狼也一直沒有辜負高曉松,唱紅了很多首歌。
後來高曉松酒駕進了監獄,老狼十分心疼,
在他出獄時,果斷送了10萬塊幫他度過困境。
當然,兩人的友情也並不是一帆風順,期間因為創作方向鬧過很大的矛盾。
其時氣頭上的高曉鬆對著老狼吼,有本事你別再唱我寫的歌。
這也讓兩人決裂了一兩年。
直到有次在酒吧偶遇,高曉松向身邊友人
悄悄介紹另一桌的老狼時,老狼拿起了杯子舉了個杯。
兩人徹底釋懷。
而今,他們的友誼也成了民謠界裡一段佳話。
有句話說,人生就像一輛列車,有人上來,就有人下去。
越長大越對此有感觸。
你看看自己身邊,這些年來,多少朋友來了又去,能留下來的寥寥無幾。
我們嘴上說著有空一起吃飯,但多數都是沒空,說著下次再見,多數都是再也不見。
其實我們心裡都明白,每個人的生活都被按下了快進鍵,我們一刻都不敢停地往前趕路。
每個人的生活壓力都比以前大了很多,除了工作時間,
我們更願意在家裡窩上一整天,即便什麼都不做,也不願約上朋友出去玩。
更何況以前的朋友和我們如今的生活閱歷大不相同,
興趣愛好見識都談不到一起去,很難做到像以前一樣。
能夠地久天長的友誼真的很少。
散場是多數友誼的最終走向。
這應該也是值得高興的一件事情。
其實我們都該明白,每段關係都有自己的期限,
永遠不要奢望每一段友誼都能達到自己理想的狀態。
有那麼一個人,你們見面頻率可以少,聊天可以少,
但能在你生命中幾個關鍵時刻都在,你需要的時候都在,那就夠了。
我知道,和朋友走著走著就散的滋味不好受,誰都會有所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