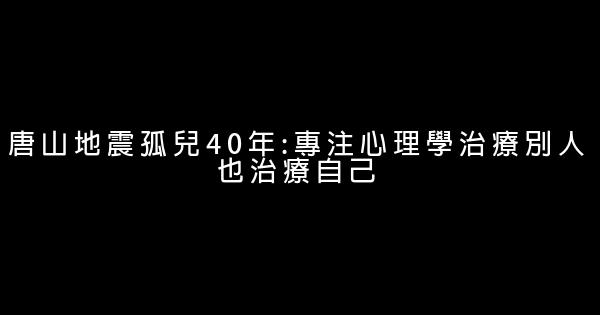董惠娟,作為國內首位災害心理學博士,治愈了不少存在災後心理創傷的病人。
董惠娟在災害心理危機干預救助中心。
7月22日,董惠娟在災害心理危機干預救助中心。
新唐山40歲。曆經滄桑的大地,生長從未停息。40年前的大地震顫,奪走24萬生靈;23秒里,繁華變烏有。時間熨平傷痛,曾經百萬人口的工業重鎮在墟土上向死而生。40年,我們再次撫觸公共記憶中的曆曆傷痕,既為悼念逝者,亦為敬畏生之信念,繁盛之決心。今日起,新京報推出“唐山大地震40周年”系列報道。我們將通過4組幸存者40年的生活日常,回顧他們自我治愈、尋親、組建家庭以及找尋自我的過程。這些源自本能的求索,恰是一座城市從瓦礫走向現代化的內生力量,更是屬於中國,乃至全世界的寶貴記憶。
治療別人,也是治療我自己。——董惠娟地震孤兒、國內首位災害心理學博士
董惠娟又看到了媽媽。
廢墟上,媽媽半截身子露在外面,跪著,雙手扶著床,想用力、起身,卻被突然掉下來的房梁壓住。她的兩隻胳膊已經充血,黑腫,像碗口那麼粗。腕上的一隻表,深嵌進皮膚里。
40年過去了,每當精神脆弱時,這個畫面就會被喚醒,一遍又一遍。
和上百萬唐山人一樣,董惠娟的命運在1976年7月28日被改變——父母兄嫂成了242419個喪生者中的四個數字,當時隻有15歲的她,成為4204名地震孤兒之一。
這40年,焦慮、抑鬱、對生活喪失希望等情緒,像幽靈一樣,盤桓在很多親曆者的心頭。
一項針對1695例唐山地震親曆者的調查顯示,在震後二十年,眾多親曆者出現創傷後應激障礙(PTSD),他們患神經症、焦慮症、恐懼症的比例高於正常人群。
董惠娟決定研究災害心理學。她說,“治療別人,其實也是治療自己。”
唐山的重建,在震後第一個十年已經完成。而人心的重建,因為錯過了心理危機干預的最佳時機,最終交給時間:漫長、持久。
好在,40年過去,唐山人一點點脫敏、淡忘,自我療愈。“人總要繼續生活。”董惠娟說。
病根
董惠娟的辦公室在255醫院的災害心理危機干預救助中心。在這里,她成功治愈了不少存在災後心理創傷的病人。
深色地毯、橘色沙發、暗色花布窗簾,董惠娟的心理谘詢室,給人一種安心的感覺——這正是心理谘詢師想給病人的第一觀感。
董惠娟現在有兩重身份,學校有課時,她是唐山師範學院一名心理學老師,上完課後,她是災害心理危機干預救助中心的主任。
董惠娟承認,她本人也有心理創傷。盡管40年過去,傷口已經愈合,但疤痕仍在。“你撥動它時,它會震顫。”
每對病人心理干預一次,她內心的傷疤就會被掀開一次,然後愈合,掀開,再愈合,循環往複,一點點脫敏。
董惠娟的病根深深紮在1976年那個炎熱的夜里。
被困7個小時後,董惠娟被大姐和大姐夫救出。目之所及,沒有一間房子是立著的,家里的小院沒了,六七間房被夷平,眼前的情景,深深刺痛了她的神經。
她站不起來,隻能在廢墟上爬行,哭喊爸爸媽媽的名字。她最早發現的人,是懷孕的嫂子,接著是爸爸、跪著的媽媽,都沒了氣息。
哥哥還有一口氣。家人想把他送到唐山豐潤區的機場搶救。董惠娟負責帶路,那條路她在兒時走過很多遍,但這一次,卻怎麼也找不到——原來的房屋、街道變成一片廢墟,沒有路、沒有路標、沒有方向。每走一步,都要扒開路邊流著血的屍體、受了重傷的人。
這些畫面深深刺在董惠娟的腦子里,伴隨的是絕望和無力感。
哥哥最終還是離開了。在地震前幾天,兄妹幾個都才從四面八方趕回來給媽媽過生日,一夜之間,一大家人,沒了四口。
董惠娟想扒出廢墟下面的父母,卻一點力氣都沒有,隻能守著。到了晚上,廢墟下的叫喊聲、呻吟聲,從四面八方彙聚,在她的耳邊縈繞。
董惠娟回憶,事後多年,那種代表著疼痛和悲傷的聲音始終縈繞在她耳邊。“很淒涼”。
父母被挖出時,已經是震後的第三天。裝遺體的卡車快開走時,董惠娟問解放軍,要拉到哪里去。對方回,很遠很遠。
後來,她打聽到,當時的遇難者都被拉到了南湖附近掩埋。但之後的很多年,她一直找,一直找,也沒有找到具體的位置。
“沒有一個可以悼念他們的地方。”7月14日下午,董惠娟聲音顫抖,拭了拭眼角的淚水,“這是最殘酷的事情。”
遺憾最終積聚成心病。每到7月28日,那些畫面、場景、聲音、味道立刻湧上來,悲慟,焦慮,好幾天都提不起精神。
創傷
父母離開之後,再小的事情,也會在瞬間把姐妹四人擊敗。
1976年的一個冬夜,姐妹四個住在簡易棚里。氣溫零下十幾度,北風呼呼地往棚子里灌。
姐妹四個抱在一起取暖。不知道誰冒出一句,真羨慕鄰居家,搭的棚子真好,有油氈,不漏風。“我們可怎麼辦?要是爸媽在就好了。”
話音剛落,姐妹四個互相對視了兩三秒,說不出一句話來,隻能抱頭痛哭。
董惠娟回憶,在震後的一兩年里,這種歇斯底里會在任何不經意的時刻出現——家里的一座古典鍾被挖了出來,姐姐立刻奪過來,喊著,人都死了,要這些東西有什麼用,搬起來,便扔了出去;在董惠娟當時任教學校的教研室里,隻要有一個老師嚎啕大哭,周圍的同事都會跟上,幾分鍾後,整個辦公室就被哭泣聲淹沒。
恢複高考後的第三年,董惠娟考入河北師範大學。一天晚上,正在宿舍睡覺,樓上傳來了“轟轟轟”的聲音。她和室友驚醒,當年地震時的畫面,像放電影一樣重現。跳下床,撒腿就跑,一路狂奔到操場,才知道,原來是樓上的同學,起夜時不小心碰到了鉛球,6公斤重的鉛球一滾,形成類似地震的聲音。
第二天上課,不少同學胳膊擦傷、下巴碰破皮,一問才知道,他們都是唐山人。晚上聽到聲音,慌了神,直接從二樓跳了下去。
董惠娟逐漸意識到,時間並不能撫平地震帶來的陰影。“我很心痛,為什麼隔了幾年,我們還是處於警覺和驚恐的狀態。”
暑假回到家,大姐總是提醒,7月28日快到了,要給父母燒紙了。在董惠娟的記憶里,每年的那一天,總是彌漫著煙霧。在唐山的每一個十字路口,都有人燒紙,黑色的紙灰漫天都是,整個城市都沉浸在悲傷的氛圍里。
董惠娟還發現,她的兩個姐姐一個妹妹,包括她自己,在7月28日前後,都會感覺情緒低落,持續一個禮拜左右才會好轉。極度悲傷時,姐妹們還會抱怨,活著有什麼意思,還是去找爸爸媽媽吧。
類似的情緒會在兩個節日重現:清明節,農曆十月一日——中國民間祭奠先亡之人的寒衣節。
董家對面的一個鄰居,地震中失去了父母和妻子。之後的一兩年里,這個中年男人每天坐在簡易房門口一會兒哭一會笑。有人和他說話,他隻會重複兩句“好好活著”、“我不悲傷”。
董惠娟那會兒總是反複咂巴他那句“好好活著”。但沒幾年,男人就過世了。
為什麼唐山有這麼多的創傷?董惠娟很困惑。她想通過讀心理學的方式,分析自己和身邊的人。
病人
和董惠娟一樣困惑的,還有開灤精神衛生中心的十幾位醫生。
醫生於振劍至今記得上世紀90年代初接觸到的一個病例。一位二十多歲的女性,到了陌生場所,如果發現門窗不能打開,就會非常恐慌。她無法正常乘坐封閉的電梯、轎車、煤礦上通勤的綠皮火車。
追溯原因,於振劍發現,大地震時,她十來歲,被埋了幾個小時,黑暗中,窒息的感覺非常強烈。被救後,這種恐懼被壓抑了,十年後,出差遇到類似的場景,心理創傷再次被激發。
時任開灤精神衛生中心院長的張本也遇到不少類似的病例,親人在地震中喪生後,不少幸存者在十多年里連續出現無法正常入睡、做噩夢、易傷感、對人生失去興趣、對未來失去信心的狀況。
醫生們發現,這些具有精神疾病和心理疾病的病人,大都經曆過唐山大地震。
1995年開始,張本帶著於振劍等十幾位醫生,針對地震對孤兒、喪偶再婚者、截癱患者、一般受難者等不同群體開展了研究,曆時十年。
數據證實了他們的猜測,地震的親曆者們患神經症、焦慮症、恐懼症的比例遠高於正常人群。在地震中承受的心理創傷程度越高,二十年後,他們的心理健康程度越低。
同一時期,董惠娟已經讀完應用心理學的碩士課程。她開始分析自己。
2000年前後,買房的壓力和兒子的叛逆期一起襲來,董惠娟覺得要被壓垮了。那段時間,她總做夢:媽媽坐在唐山一處地下通道的入口處向她招手,她跟在媽媽後面,沿著漆黑的地下通道,一直走,一直走,越走越亮,接著,媽媽就消失了。
後來,在博士論文進展不順利、被家庭瑣事纏身時,她總會做這樣的夢,有時是地震前一家人給媽媽過生日的畫面,有時是媽媽送她上學的場景。
她分析,每當精神脆弱時,就會出現夢魘和閃回。而創傷的根源在於,成長中,她缺乏父母的支持。
在北京、上海學習時,別人一聽她是唐山人,總會好奇家里有沒有人受傷。“我從來不會告訴別人,那個傷痛是不想被別人扒的。”董惠娟說。
事後她知道,在心理學上,這叫“回避”,也是心理創傷的一種。
她嚐試自我調節。每天早上,跑到廣場上跳集體健身操。“大家伴隨音樂一起跳起來時,內心會有一種滿足感。”後來,得了風濕,跳不動了,就去逛商場,隻看不買。現在,她幾乎能認全商場里的所有品牌。
2004年12月,印度洋海嘯,董惠娟正在中國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讀博二。她和同伴們趕去心理援助時,又看到了一具具泡得發脹、發白的屍體,到處都是災民,表情恐慌。
她發現,災難場景並沒有勾起她關於唐山地震的回憶,這意味著,她已經開始慢慢走出之前的心理創傷。
關於唐山地震的親身經曆和前輩的問卷調研、印度洋海嘯的心理援助經曆,成了她博士論文的重要組成部分。
2006年,她終於拿到博士學位。所攻讀的方向,也是和她的命運緊密相連的災害心理學。
在博士論文的扉頁,她寫道:“僅以此文獻給養育我成長的父母。這麼多年來,他們的在天之靈一直在給予我支持和鼓勵。”
援川
包括董惠娟、張本等在內的學者一直都覺得,1976年,由於社會環境和醫療條件所限,導致震後心理救援缺失,造成了太多存在創傷後應激障礙的唐山病人。
這是董惠娟的一塊心病。
2008年汶川地震,她找到了出口。
那一年,唐山派出了大批救援隊伍、心理救援團、醫療工作者支援汶川。
董惠娟是唐山第一批到達汶川心理援助的14名隊員之一。5月15日,抵達綿竹。她回憶,滿眼都是受傷的災民、救援的部隊,這和1976年的唐山類似,但她已經沒有任何心理不適。運送物資的車輛在路上排著長龍,這讓她覺得,國家目前的經濟狀況早已不是唐山地震時的狀態了。
“我當時滿腦子都是,救人!”她想,當年,唐山人沒有災害心理應急救援留下了遺憾,汶川人不能再有了。
同一批參加心理救援的華北理工大學心理學院教授楊紹清發現,作為唐山地震的親曆者,在汶川做心理援助,很有優勢。“親曆者的說法,會讓他們的恐懼消除很多。”
楊紹清記得,很多心理救援的隊員,都是揭唐山地震的傷疤去治療汶川地震的創傷。
在汶川的39天,董惠娟對數不清的災民做了心理干預。看到父母雙亡的孩子,她總會下意識地說“我也是地震孤兒”。一句話,瞬間拉近了雙方的距離。
讓董惠娟印象深刻的是一個截肢的17歲花季少女。董惠娟是在一個溫度高達50攝氏度的帳篷里發現她的。女孩已經21天沒有走出帳篷了。
董惠娟走上去,剛想把手放在女孩的右腿上,突然發現,穿著白色褲子的右腿空蕩蕩的。寒暄後,女孩哭著強調,她再也穿不了裙子了。
經過幾十分鍾的心理干預,女孩走出了帳篷。
那是中午,陽光炙熱。董惠娟站在女孩對面一米遠的地方。但女孩拖著一條腿往前跳,幾次摔倒,又幾次爬起來。董惠娟站在對面,心絞著痛,跟女孩說,加油,加油。
最終,女孩蹦跳著撲到董惠娟懷里。女孩哭著說:“阿姨,是你又讓我活了過來。”
董惠娟一直和女孩保持著聯系。如今,女孩裝上了假肢,恢複了正常生活,還在一家酒店當上了經理。
董惠娟團隊從2008年連續跟蹤汶川四五所學校、2000多名學生的心理狀況。數據顯示,在最開始的幾年,孩子們的焦慮、恐懼、抑鬱、偏執等指標都比較高。從2011年開始,各項指標逐漸回到正常水平。
她覺得很欣慰。汶川地震,可以算是她災害心理學理論的一次成功的應用和推廣。後來,她又在唐山255醫院掛牌成立了災害心理危機干預救助中心。
她希望,心理救援能成為常態,出現災害時,心理專家能及時介入,幫助更多人。
自愈
董惠娟也知道,汶川心理援建的成功,是建立在唐山的遺憾基礎上的。
震後,唐山人在自力更生的口號下,重建和振興城市,整整花了二十年。而心理重建,在震後二三十年,依舊是相當陌生的詞彙。
唐山截癱療養院副院長張希成記得,1988年,他剛到療養院工作,病人情緒不好,一般認為,病人需要做“思想工作”了。兩年後,一個不到40歲的病人自殺,大家都以為,這位病人是受不了截癱引發的並發症。直到後來,一個留學生來做心理測評,他們才知道,病人可能需要系統的心理干預。
在唐山重建中,針對地震孤兒、截癱患者,政府采用了家庭領養、集中療養等方式,幫助恢複家庭和社會功能,心理重建。
張希成覺得效果不錯,“現在療養院的老人心態都很平和。”
華北理工大學心理學院教授程淑英還發現,和其他地區相比,唐山地區學心理學的人相對較多,熱情高漲。“可能是出於一種心理上的需要。”她總結。
和董惠娟一樣,治療別人,也治療自己。
張本承認,作為地震的親曆者,他也有焦慮、抑鬱等心理障礙。這也是他曾經持續研究唐山地震對親曆者身心健康影響的原因之一。
“但更多的人意識不到。”張本說,心理創傷會一直在記憶里存儲。還有很多人在壓抑這種痛苦。
7月15日這一天,董惠娟又接到很多電話,來自廈門、天津,谘詢建立心理救援機構相關事宜。
董惠娟覺得,越來越多的人關注心理救援、心理健康,是很好的趨勢。
如今,她和丈夫都是同一所大學的老師,兒子已到而立之年。姐姐和妹妹也都有自己的家庭。很少再有困厄、無助、出現閃回和夢魘的時刻。隻是提到父母離去的場景,偶爾還會刺中心里最柔軟的部分。
2006年後,她又做過一次研究,近5000份問卷顯示,在震後三十年,仍有70%的受訪者或多或少存在創傷後應激障礙(焦慮、抑鬱等)。而在震後十年,她對身邊的親曆者做訪談時,這個數字幾乎是100%。
“震後40年,這個數據應該還會下降。”董惠娟說,隨著時間流逝,人們慢慢自愈。
7月15日傍晚,唐山市中心的抗震紀念碑廣場上,有人乘涼,有人追逐嬉戲,有人跳廣場舞。紀念碑前,放著一束白菊,還在提醒著這座城市40年前發生的一切。
在廣場上乘涼的熊女士,今年68歲,她清晰地記得40年前那個夜晚發生的一切。她習慣性摩挲著右手無名指關節上的傷口——盡管早已愈合。
“這麼多年,已經沒感覺了。”她說,“都過去了。”